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1-07-22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321次
摘 要: [摘要]平台经济对网约工集体劳动权的行使提出了挑战。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形成于大工业时代,工会会员资格与劳动关系结合紧密。平台经济颠覆了企业传统用工方式,网约工面临劳动者身份认定困境,既难以加入企业工会,又难以通过基层行业工会与跨区域经营的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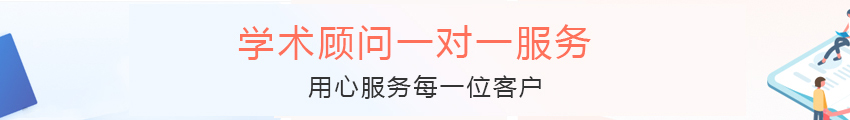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平台经济对网约工集体劳动权的行使提出了挑战。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形成于大工业时代,工会会员资格与劳动关系结合紧密。平台经济颠覆了企业传统用工方式,网约工面临“劳动者”身份认定困境,既难以加入企业工会,又难以通过基层行业工会与跨区域经营的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研究认为,面对平台经济引发的挑战,有必要破除劳动关系“迷思”,将网约工纳入“生存权”进路下的“职工”范畴,为其组建或批准跨区域的高层级行业工会,探索与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的方式,以工会治理现代化回应网约工集体劳动权保护需求。

[关键词]平台经济;劳动关系;团结权;行业工会
“没有边界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持续深入地改变了我们所认知的世界,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出现了通过网络平台对不特定的群众进行摄合的众包工作[1],对企业的经营模式、用工方式等均产生了颠覆式影响,其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避免地回射到以劳动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劳动法。检视2015年以后的论文a,平台经济已成为劳动法研究的热点,学界研究多指向与劳动关系贴合更为紧密的个别劳动法,以描述性“网约工”概念为切入点,讨论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者分类等问题[2-3]。相较之下,从集体劳动法角度研究的成果较少。当前研究主要指向网约工在集体劳动法上的身份定位[4],缺乏对业态变迁之下网约工团结权行使途径的深入探讨,更遑论之后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行动。集体劳动法作为“劳动力提供者”权利保护的机制之一,是劳动法的重要起源和基本类型。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基于法和社会变迁之框架[5]探讨平台经济引发的业态变迁,分析这种变迁对网约工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特别是团结权的影响,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之下提出可能的应变之道。
一、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与业态变迁的一般关系
正如德国学者瓦尔特曼所言:“如果人们不从劳动法历史发展的背景出发,不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背景出发,不通过开放的,但同时也是有保留的对在有关‘正确劳动法’的争论中激起的利益政策的观察来思考劳动法,人们就无法理解劳动法。”[6]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以集体劳动法律管制为基础框架,其形成是为了因应特定商业形态下劳动关系出现的问题,这一点通过回溯历史发展,可以得到清晰映象。
古典劳动法律管制形成于19世纪的英国,根植于工厂法。当时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合同,工厂通过与工人个别签订劳动合同,大量雇用工人在厂区集中劳动。尽管单个契约自由所要求的合同当事人双方力量均衡的情况并不存在,但立法者仍然坚持在劳动合同方面按照私人自治的原则进行立法,因此,单个的雇员仍然继续受到力量强大的雇主的强制命令的制约。由此引发了种种恶劣现象:低工资、长工时、在男人持续失业的同时使用女工和童工、缺乏劳动安全保护、在供养者生病或死亡时缺乏社会保障。为了同这样的现象作斗争,立法首要保障的就是雇员的团结权,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生工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赋予工会合法地位的国家,时间是1824年[7]。此时期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劳动力提供者需要具有雇员身份,会员资格与劳动关系结合紧密。以英国为例,当时的《工会法》调整的就是雇员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雇员”享有结社权。与英国相似,美国的《国家劳动关系法》作为管理私人企业劳动关系的主要的联邦法律,赋予“雇员”权利成立劳工组织,雇员身份也是参加工会的基础条件[8]。二是虽然存在企业工会与行业工会的不同类型,但鉴于一个工厂内可能存在多个行业工会,其相互竞争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9],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国,企业工会逐渐成为雇员行使集体劳动权的主要机制。
商业形态一直处于变迁之中,但直到互联网时代到来,甚至直到互联网3.0到来之前,业务变迁影响的主要是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方式,并未对企业用工形式产生根本影响[10]。“雇员”“劳动者”这样的基础性概念虽然亦曾受到“劳务派遣”“外包”等形式侵蚀,但核心指标是稳固的,真正对传统用工关系乃至劳动者身份产生颠覆式影响的是基于互联网3.0运营的平台经济,下文将结合案例,展现平台经济引发的变革。
二、平台经济用工模式转变与网约工集体劳动权行使困局
(一)自由与控制的错裂:平台经济用工模式解析
1.“去劳动合同”:网约工劳动力提供与抽离的自由
传统业态之下劳动合同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是仲裁机构和法院划分及确定双方责任的重要依据[11]。企业通过与劳动者定约,集中劳动,施加管理,以企业名义对外提供产品或服务。与传统业态不同,各类众包平台多主张其提供的是“摄合”服务,“摄合”的对象是网约工和用户。以众包速递平台“闪送”为例,其由北京同城必应有限公司开发,2015年上线,工商注册的所属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等。同城必应公司的业务定位为“公司运营闪送平台,用以解决客户关于小件物品寄送需求与社会上闲散运力之间无法有效对接的矛盾”。在信息平台的自我定位之下,“闪送”采用众包模式招募“闪送员”。从平台企业的视角,这些闪送员是网约工,“公司提供的是平台,由客户下单,闪送员自愿接取订单,闪送员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a。公司对闪送员的工作时间,如每月最低在线天数、每日最低在线小时并未作出要求,亦未对闪送员的工作地点和配送、接单区域等作出规定,闪送员接单的方式为:打开手机,登录APP,开启“听单”模式,平台推送订单,其本人“看哪个活儿好抢哪个”[12],在是否从事闪送以及何时接单、何时休息,甚至注销闪送账号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如果闪送员不想继续为平台工作,可以随时注销账号,也可以不注销账号但不登录不接单,单就形式而言具有劳动或不劳动的自由。
2.过程中的信息控制
尽管网约工可以自由注册、自由注销,但只要其进入接单状态,平台就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对其进行至少两个维度的控制。
第一个维度的控制是行踪监视。行踪监视是当前平台企业普遍采取的过程控制措施。同样以闪送为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全程监控闪送员端位置,平台亦同步监控闪送员的行踪,这是平台为确保物品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这种行踪监管已引发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有学者认为行踪监视涉及多种权利的冲突,例如雇主的劳动指挥权、设施管理权与劳工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当平台透过GPS等科技技术监视这些网约工的行踪,了解其执行职务的状况并进而作为奖惩的依据时,实质上正强化了这些自营作业者的人格从属性而使其有适用劳动保护法的可能性[13]184。
第二个维度的控制是用户评价反馈及相应奖惩。传统模式之下企业管理者通过制定绩效评价等多种手段评估劳动者的劳动效果。平台模式之下企业通常不直接与网约工发生“物理”联系,不对网约工的工作进行直接的评价和管理,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引入了新的评价主体——用户,平台企业借助互联网系统和大数据信息收集等优势,建立起以信用评价和打分为主的用户管理机制。并且,这种用户管理机制设计有利于帮助平台降低匹配成本[14]。平台可以依据用户评价,奖励有信誉、服务质量高的网约工,减少或停止对评价差的网约工的派单,这会导致该网约工工作机会减少,从而影响其收入。企业也可以依据用户评价或者网约工接单情况对其进行奖惩。
综上,相对于传统企业以劳动合同为载体的雇佣形态,平台企业的用工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约工上下班表现为形式自主的“上线”与“下线”,相应的平台对劳动控制变得更加碎片化,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的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15]。
(二)网约工集体劳动权行使的双重困局
1.网约工难以加入企业工会行使集体劳动权
工业时代,“多数劳动者是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劳动场所),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16],客观上具有建立人际联结和行使集体劳动权的时空场域。平台用工所具有的“自由与控制的错裂”,使得网约工和平台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成为异常复杂难辨的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依据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了包括管理标准、报酬标准、生产条件标准和其他因素在内的4个判断标准。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综合考量这4个标准,不仅关注某一网约工是否受到了平台企业的管理,亦会关注生产工具的来源以及管理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等。以2019年于某某诉闪送平台案为例,该案中法院认为于某某在快递业务选择、工作时间和报酬分配等方面均不受平台企业的管理和支配,且劳动工具亦未由平台企业提供,因此于某某与闪送平台不属于劳动关系抑或劳务关系a。除了客观因素,网约工的“意思表示”亦会影响劳动关系的判断,当前平台在网约工注册时均将“同意”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作为注册的必要条件。在2019年郭某某诉闪送平台案中,法院认为“郭某某在注册成为闪送员之前知悉并同意了《合作协议》,而该《合作协议》已经明确载明双方间并非劳动关系。换言之,如郭某某对《合作协议》持有异议,其完全有权停止、不再进行后续的注册行为;但郭某某在明知《合作协议》已排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仍自主完成了后续注册行为”b,结合对劳动过程的审查,法院认为郭某某与闪送平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去劳动关系”的结果是,网约工不是平台企业雇用的劳动者,不具有员工身份,无法加入平台企业的工会,无法通过企业工会行使集体劳动权。
2.践行中的基层行业工会难以代表网约工与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
2018年,为了解决没有劳动关系的特定劳动群体入会问题,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体”入会工作,其中人数庞大的“网约送餐员”是“网约工”的类型之一。从各地的实践看,为“八大群体”建基层行业工会是吸收其入会的主要方式,如上海市总工会建立了包括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在内的9个区级行业工会[17],佛山市成立了物流快递电商货运行业工联会[18]。相较于街道工会,新组建的区级或市级行业工会是“八大群体”入会的主流形态。目前亦有行业工会代表某一群体与企业成功进行集体协商的案例,例如,2021年初经过近半年的集体协商,陕西宝鸡市快递行业协会的7名职工代表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保险福利等与7家快递企业签订了“一合同三协议”[19]。但就网约工而言,其所加入的基层行业工会固然可以发挥传统的“送温暖”功能,但是难以代表其行使集体劳动权。目前新组建的行业工会多数建在区一级,最高到市一级。而从平台企业的运营来看,跨区域是其中一个显著特点。以“滴滴出行”为例,其北京总部以5万左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量服务器支持全国范围内的运营,其他省市即使在基层组建网约车司机行业工会,也难以与“滴滴出行”等跨区域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开展集体协商。同理,佛山的“网约送餐工”确实可以加入当地的物流快递电商货运行业工联会,但该行业工会同样面临着与总部在上海的“饿了么”平台以及其他外卖平台开展集体协商的难题。
概言之,目前网约工缺乏有效行使集体劳动权的机制,“平台用工的灵活化多元化分散化,使像散沙一样散点分布的网约工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能力趋于弱化,个别平台居于行业垄断地位,原子化的网约工几乎没有与其博弈和议价的能力”[20]。如果不作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网约工将面临着集体劳动权的失保护,被迫回归“丛林法则”。
三、基于中国工会体制的网约工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革新
(一)平台经济背景下中国工会体制的优势
1.以“职工”而非“劳动者”作为加入工会的基础概念
我国《工会法》第2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职工”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里的劳动者包括但不局限于2008年《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者,《工会法》第3条提出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识别标准是“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工会法的主旨,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工资劳动者的权利”[21]172。
《工会法》以“生存权”而非“劳动关系”作为界定会员资格的进路,赋予了工会会员以弹性扩展的空间,尽管业态可能风云变幻,但只要某一行业的劳动力提供者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就可以将其纳入《工会法》第2条的“职工”范畴,保护其集体劳动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工会法与我国认识相近,日本《劳动基准法》界定的劳动者是指不问职业的种类,接受事业单位的雇佣,并受领工资的人;而《劳动组合法》界定的劳动者则指不问职业的种类,依靠工资、薪金及其他类似收入而生活的人[22]。二者区别在于《劳动组合法》上的劳动者不一定“接受事业单位的雇佣”,仅“依靠工资、薪金及其他类似收入而生活”即可,其采用的亦是生存权标准。
2.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各级工会有能力和资源积极回应业态变迁
我国实行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元工会制度[23],“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工会具有“人民团体”身份,不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适用对象,上级工会机关被更深地整合进正式的国家架构[24],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这是我国工会体制的突出特色。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会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特征,既有作为国家工具的国家属性,又有作为工人组织的社团属性[25]。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各级工会有能力和资源回应新业态提出的挑战,我国集体合同制度推进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依法成立的工会具有当然的代表权
中国工会的权力一直源于其在党政系统中的合法身份和地位[26]。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之下,依法成立的工会具有当然的代表权,不存在行使集体协商的资格障碍,中国工会代表的对象除了会员外,还可以代表非会员利益[27],在平台经济下,这是中国工会体制的突出优势。从国外的实践看,韩国、日本等国的网约工也尝试组建行业工会,这些自行组织的行业工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代表权”难题。以日本为例,其《团体协约法》第6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了协商资格,以致网络平台等业者如果拒绝与没有达到其所使用的同类网约工人数二分之一以上者所加入的产业工会进行团体协商时,该产业工会无法主张平台业者构成同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无正当理由拒绝团体协商。如此的协商资格要求对产业工会及其会员的团体协商权行使构成了重大的限制,使得网约工及其所加入的行业工会要取得协商资格困难重重[13]189。中国工会所具有的组建主动性、代表广泛性的特点,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和运作空间。
相关知识推荐:职称评审发表论文多了好吗
(二)革新的路径
1.破除劳动关系迷思,将“网约工”纳入“职工”体系
传统观点认为工会的产生必须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因为没有劳动关系,就没有职工,自然更没有工会。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或雇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劳动关系的引申和发展[21]172,此观点将加入工会资格与劳动关系绑定,在工厂制为主的业态模式下或许不存在问题,但在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下,会导致网约工集体劳动权的失保护。当前网约工中的绝大多数是以平台扣除信息费后的报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网约工获得的报酬类似于计件工资收入,符合《工会法》上的以生存权为标准的“职工”界定,不论其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都应认定为“职工”,有加入工会的权利。
2.为网约工组建与平台经济相适应的高层级行业工会
行业工会不同于《工会法》第10条提出的产业工会,《工会法》第10条对产业工会的规定是“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的几个行业,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全国的或者地方的产业工会”。产业工会在逻辑上包括行业工会。作为基于职业的组织体,行业工会的历史早于产业工会,如我国民国时期的“理发工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提出“按产业建工会是工会组织的基本原则”[28],但由于当时企业形态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企业和工人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企业工会成为更主要的工会形态。平台经济所具有的“去劳动关系化”特征凸显了为网约工组建行业工会的必要性。
就网约工而言,从代表其开展集体协商的角度,对同时需要与几个跨区域的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的行业,宜在全国总工会之下组建一级行业工会,或者至少在省级组建一级行业工会,报全国总工会批准。关于此类行业工会的领导体制,当前《中国工会章程》第11条规定:“除少数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的产业,其产业工会实行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双重领导,以产业工会领导为主外,其他产业工会均实行以地方工会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产业工会领导的体制。各产业工会的领导体制,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面向网约工的行业工会不宜采取“以地方工会领导为主”的体制,更宜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网约工所在行业特征,确定其领导体制。
3.探索网约工入会和集体协商的新模式
为方便网约工入会,可借鉴近年全国总工会“智慧工会”建设的成果,将“互联网+”融合平台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开发平台产业工会APP,方便网约工申请入会,通过APP向网约工推送服务,为其网上维权提供便捷渠道等,以服务提升网约工入会的积极性。成立后的行业工会,应当积极与平台企业接触,就网约工关心的商业保险的购买方式与费用负担,提成比例问题、奖励和惩罚的原则问题等与企业展开集体协商。实践证明,对于官方工会发起的集体协商,特别是级别高的工会,企业往往比较重视,可以为代表的职工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而集体协商的成果可以吸引更多的网约工加入行业工会,赋予其行使集体劳动权的机制。
四、结语
平台经济的崛起已是不争的现实。当下劳动法不乏主张扩展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将网约工纳入“劳动者”范畴的观点。然而,过度严格地将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拉回大工业时代的劳动法管制下,不仅有消亡平台经济新业态的风险,而且可能非部分网约工所愿。例如,美国加州2020年开始实施的AB5法案就受到了来自加州卡车司机协会等群体要求免除适用的诉讼,尽管该法案使得平台工作者更容易被认定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但显然卡车司机们更愿意保持“自雇”身份。相较于个别劳动法的扩展,创新集体劳动权行使机制,向网约工提供集体劳动法上的保护可能更符合网约工的利益,且组织化可以改变网约工“原子化”的状态,加强其相互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不仅具有劳动法上的意义,且具有满足个体“社会融入”的功能。在此领域,我国工会具有代表性、组建主动性,更易于回应平台经济提出的挑战。通过创新平台网约工行业工会,将网约工纳入中国工会的组织体系,保护其合法权益,将是“60年来中国工会三次大改革”[29]之后迎来的第四次大改革。——论文作者:杨欣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