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4-09-15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234次
摘 要: 摘要: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的法院怎么能够对那个案件行使管辖权呢?或你们的法院对那个案件为何不能或不会行使管辖权?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律师看来,似乎美国法院会受理那些本不应由其受理的案件,而不受理那些本来应该由其受理的案件。本文将试图阐述美国法院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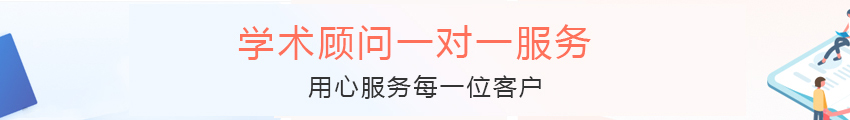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的法院怎么能够对那个案件行使管辖权呢?”或“你们的法院对那个案件为何不能或不会行使管辖权?”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律师看来,似乎美国法院会受理那些本不应由其受理的案件,而不受理那些本来应该由其受理的案件。本文将试图阐述美国法院受理和不受理一些案件的情形和依据。
一、管辖权
在欧洲大陆法国家和那些以大陆法为法律模式的国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法院审判案件的权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两方面:事物管辖和地域管辖。前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被授权审理那类案件的法院,后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与案件当事人、事实经过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联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同时具备以上两方面,则该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英美法系关于管辖权(jurisdiction)的概念与大陆法系的管辖权(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细微的不同。我们的管辖权也包括事物和地域两种因素。一个纠纷必须诉诸于有事物管辖权的法院,即案件必须属于法院被授权审理的案件的一种。然而,除此之外,对双方当事人法院还必须有对人管辖权(如果是对人诉讼)或对物管辖权(如果是对物诉讼)。管辖权中的地域因素体现在对人管辖权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对一方当事人行使对人管辖权之前,该当事人必须与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权领土有一定的联系。
州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而联邦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却是有限的。联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数特别种类的案件,如基于联邦法律产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一州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然而,州法院却可以受理除少数专门由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种类的案件。就事物管辖权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萨斯州,一般初审法院都可以受理一个日本公民和另一个日本公民之间因合同违约所产生的纠纷案件,尽管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要想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法院,对人管辖权是限制法院权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与大陆法系国家着重考虑对案件的管辖权不同,我们所考虑的主要是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如果一个被告自愿接受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则不需要在他与诉讼法院之间有地域上的联系。但如果对管辖权有异议,则原告必须选择一个与被告有适当联系的法院起诉,只有该法院才能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假设一个被告在一个主权领土范围内有自己的家,而该地的法院正在寻求对其行使管辖权,则这个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允许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合适连结点。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并不是唯一的连结点。
在历史上,英美普通法认为,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一个功能。如果一个法院能拘捕某个人,则此人隶属于该法院的管辖权。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诉讼确实是从对被告的人身拘捕开始的,被告被关押直到案件审毕。后来,实际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对待被起诉的刑事罪犯一样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过传票传唤被告。传票表明,如果必要时,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个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非当地居民,当他出现在法院辖区,并被以合法的程序传唤时,其也可能隶属于该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因此,被告与法院之间的适当联系包括三种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辖区,被告放弃管辖权异议;被告出现在法院辖区。这些在过去被认为,现在也仍然被认为是确定对人管辖权的传统基础。在著名的Pennoyer诉Neff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三种传统的基础是宪法所允许的仅有的基础。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确定对人管辖权的这些传统基础是宪法性概念“正当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相应地,Pennoyer诉Neff一案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即州法院不能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除非该被告自愿接受管辖,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该州,或当其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
该案严格限制了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即一个法院不能随意行使管辖权,除非当被告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然而,普通法认可一种可以规避这种限制的途径,如果被告在该州有财产。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虽然是对人诉讼所要求的,但在对物诉讼中却无此要求。对本辖区内的财产,法院可以决定其所有权归属而无需享有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财产位于该州是法院对该财产享有管辖权(通常被称为“对物管辖权”)的充足根据。
对物诉讼是指决定财产利益归属的诉讼。请求被告给付金钱的诉讼或要求被告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诉讼是对人诉讼。然而,普通法发展了一种理论,该理论允许原告把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当作对物诉讼来起诉。如果原告关于金钱赔偿的请求是有效的,则原告对属于被告的财产享有潜在的利益。如果原告胜诉,而被告却没有执行该判决,则原告可以变卖被告的财产以执行判决。另外,关于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也可能被当成这样一种对物诉讼,即在该诉讼中,原告针对被告的某种特定财产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个被告享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地区起诉,即使被告不隶属于该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此种意义上的“财产”也包括被告的债权。法院只要能够对被告的债务人行使对人管辖权,就可以对由该债权所代表的财产行使对物管辖权。获得这种被称为“准对物诉讼”的机会为规避Pennoyer诉Neff一案所确立的对人管辖权的严格条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径。这种准对物诉讼的判决的效力只是给予原告变卖被告某种特定的财产以满足自己诉讼请求的权利,判决的执行不能针对被告的其他财产。
二、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的缺陷
这种依靠法院的实际支配权力去执行判决的管辖权理论的缺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对法人的管辖权。法人是没有自然属性的,它只是一种观念,但法人可以拥有财产。因此根据“准对物诉讼”理论,在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中,任何法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都将对法人财产享有对物管辖权。但是在对人诉讼中,如何确定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当地法人的对人管辖权呢?如何认定一个法人在某法院辖区出现过呢?美国立法者们的回答是,如其现在常做的一样,求助于法律的拟制。如果法人的一个机构在该州经营着其公司的业务,则表明该法人出现在该州。因此,一个法人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就隶属于诉讼所在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放弃管辖权异议;在该法院所在州注册登记;在该州“经营业务”。但此种意义上的“经营业务”从来也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于是,涉及“经营业务”意思的判决已经有成千上万。
另一方面,汽车的发明使该种理论的缺陷更加明显。汽车能使人们很容易地从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车是危险的交通工具以及许多诉讼的起因。汽车增加了这种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卷入到另一州的损害赔偿诉讼之中的可能。驾驶汽车进入乙州并在那里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导致的诉讼案件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证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证。但是按照“权力支配”理论,除非在离开乙州之前被合法传唤,一个持异议的甲州居民是不隶属于乙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的。问题的解决再次运用了法律的拟制。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些法规规定,任何人一旦在该州的道路上驾驶车辆,就意味着同意接受该州法院对任何由此行为引起的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这种拟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诉Neff一案以及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同时,最高法院也坚持认为,这种“非居民驾驶者的法规”在Hess诉Pawloski一案中是合宪的。
当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求助于某种法律拟制,去调和常识性的结论与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论之间的关系时,那么这种法律理论一定存在某种问题。在1945年对“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最终改革了对人管辖权的理论基础。
三、最起码的联系和基本的公正
“国际鞋业”一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设立在密苏里州的公司能否在华盛顿州被起诉?该公司认为,其在华盛顿州的机构的行为并不构成“经营业务”,因此该公司没有出现在华盛顿州。在反驳此种辩解时,最高法院给予“正当法律程序”在对人管辖权问题上的含义一个全新的描述:
“在历史上,法院在对人诉讼中的管辖权产生于其对被告人身的实际支配权力,因此被告出现在法院所管辖的地域内是被告受法院判决拘束的前提条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传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仅是,如果被告没有出现在法院的辖区,法院要想使其服从对人诉讼的判决,则被告与法院之间应有某种最起码的联系。因此,该案件的审判就不会与传统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触。”
伴随此种新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标准,最高法院认为,符合法律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在“国际鞋业”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没有作此种区别,除非州法规把管辖权限制于案件的起因产生在该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驾驶者”法规。如果被告出现在该州或住在该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诉,无论案件与该州是否有联系。但是在有法人参加的诉讼中,“国际鞋业”认为:“出现”只是一种拟制,被告必须与该州有某种联系。如果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该种联系,则即使是单一的孤立的联系也足以使被告隶属于该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如果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和实质性的,则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诉,无论该案由产生于何处。
究竟什么样的单一的或孤立的行为能满足合宪的最起码的联系的要求,从而支持产生于这种联系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特别管辖权”)呢?究竟什么样的系统的连续的行为是充分的实质性的,以致能够支持与该种行为无关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一般管辖权”)呢?最高法院在“国际鞋业”一案中指出,答案取决于“与正当法律程序所要保证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关的行为的性质和质量。”这被理解为“利益平衡”。与如果案件不能在那里被起诉原告所将面临的困难相比,被告在一个被选定的法院应诉究竟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呢?在允许案件在原告所选定的法院继续审理是否公正与合理的问题上,诉讼的方便是要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文所关心的正是公正与合理。
正当法律程序的新标准起源于“国际鞋业”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种联系。如果没有,则管辖权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确实与法院所在州有某种联系,则仍须查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如果是,则要进一步查明被判决所影响的利益是否允许这种管辖权。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辖权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则该法院可继续其对案件的审理;如果管辖权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则法院应撤销该案件。
如果诉讼的起因并不产生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则需要确定是否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实质性的,以致于能够使被告在缺乏与诉讼的起因相关的联系时,在该法院应诉是公正和合理的。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种依赖于利益平衡的法律标准似乎显得有些不可预测。不同的法官对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法官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对产生于“国际鞋业”一案的管辖权的分析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四、州法院管辖权的扩大:长距离法规
“国际鞋业”一案的判决为扩大州法院的管辖权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开始适用一些法规,允许其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诉讼管辖权,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对被告进行了合法的传唤。这些法规被称为“长距离法规。”其中一些专门用于识别某种可能导致被告隶属于“长距离管辖权”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广泛宣称,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与宪法相一致的基础上对被告行使管辖权。
五、故意获得和商业流通理论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诉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个关于土地标记的判决。该案宣布了对“国际鞋业”一案规则的一条限制。即使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被告与该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即使该法院是一个便利案件审判的法院,该法院也不能对被告行使管辖权,除非引起诉讼的联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的结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质的一点是,被告是有意地为某种行为,以取得在诉讼所在州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进而得到该州法律上的利益与保护。”
这种“故意获得”要求,给各州法院试图对产品质量责任案件中的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长距离”管辖权造成了障碍。缺陷产品在一州的出现常常不是产品制造商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些批发商或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但是州法院发展了一种理论,以允许对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管辖权,而置“故意获得”要求于不顾。如果制造商有意将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清楚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在诉讼所在州销售和使用,则该行为等同于将产品直接投入该州,尽管产品在该州的实际出现是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制造商有意使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而诉讼的起因产生于此,则该制造商应该服从该州法院的管辖权。
这种“商业流通”观点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Hanson案件中“故意获得”要求的真实含义是,被告应能预见其引起诉讼的行为可能在诉讼所在州产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援引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以允许法院对一个自身行为远离诉讼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辖权。《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三十七节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实施的行为在该州产生了某种效果,而诉讼的起因又产生于该效果,则该州有权对其行使管辖权,除非这种效果的性质和此人与该州关系的性质使该管辖权变得不合理。”但是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对“故意获得”要求而言,被证明是过于宽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诉Woodson一案是几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马州起诉的一起产品质量责任案件。原告从纽约州的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奥迪”牌汽车。当原告驾驶该汽车从纽约经俄克拉荷马驶向其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家时,奥迪车后部被另一辆车撞坏并起火,几个原告严重受伤。于是他们对该车的制造商、进口商、东海岸地区的分销商和零售商一并提出了起诉,诉称损害是由设计上的疏忽造成的。制造商和进口商都没有对俄克拉荷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分销商和零售商却不同。
俄克拉荷马州的法院坚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销商应隶属于其管辖权,因为法院认定他们能够预见在纽约州售出的汽车在俄克拉荷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但并不反对“商业流通”理论:“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种可预见性,不仅仅是某产品将出现在诉讼所在州的可能,更应当是被告的行为及被告与诉讼所在州的联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预测到他将在那里卷入诉讼。如果制造商或分销商的产品销售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其直接或间接使其产品进入其他州市场的努力的结果,则使其服从于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辖权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该缺陷产品是导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伤害的原因。”
在针对产品制造商提起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可预见性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产品在诉讼所在州使用的可预见性却不足以准许在该地对零售商起诉。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属产业诉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业流通”理论。该案件产生于加尼福利亚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的一只轮胎爆炸,其驾驶者被严重炸伤,他的妻子(当时也在摩托车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车的制造商和摩托车轮胎的制造商(一家台湾公司)提起了诉讼,而这家台湾公司却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轮胎活门的制造商)为被告,并辩称:如果轮胎有缺陷,其原因在于轮胎所使用的活门有缺陷;如果台湾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则日本公司有义务赔偿台湾公司。虽然原告没有向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诉,但台湾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张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应撤销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鉴于“商业流通”理论,管辖权成立。法院认为,该日本公司对其在亚洲卖给台湾公司的相当一部分活门可能被组装到轮胎上并在美国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该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认为,即使该日本公司有意建立与加州的联系,并因此引发诉讼,但利益平衡规则使要求该公司到加州应诉显得很不公平,其与台湾公司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亚洲,审理他们之间的争议案件与加州的利益毫无关系。即使台湾公司胜诉,该判决在美国也难以得到执行,同时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认并执行该判决。因此无论是要求该日本公司到加州应诉,还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该诉讼中充当陪审员,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认为,该日本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并非其“故意获得”行为的结果。该公司把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被组装到摩托车上并被在加州出售,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还应当有其他属于被告的并能表明其有意使产品进入加州市场的行为,例如广告。可见O’Connor法官对“商业流通”理论基本持反对态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确认了“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赞同以上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因此,Asahi一案的判决给“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种疑问。在后来的案件中,一些法院采用了O’Connor法官的观点;而另一些法院则站在Brennan法官一边,后者可能更多一些。毕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业流通”理论,当作一种在针对可预见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制造商提起的诉讼中,能够满足“故意获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也从来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
六、举证责任和公正
我们已经知道,对人管辖权的合宪性的现代分析,要求法院去发现被告与诉讼所在州之间有意建立的联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牵涉到的各方利益,从而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对被告行使管辖权是否公正与合理。问题在于:谁应承担这种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原告还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对Burger King公司诉Budzewicz一案作出判决之前,通常认为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是原告的起诉导致了法院对案件的管辖。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却要求被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与诉讼所在州之间的最起码联系的事实被确定,这些联系在参照其他因素的同时,就可以被用来考虑并决定对人管辖权的维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获得该案的管辖权,被告就必须举出强有说服力的判例,以证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诉讼所在州的管辖权变得不合理。”简言之,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已经有意与某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案件的起因又产生于该联系,则向法院证明其管辖权的行使并不公正的责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担。
七、传统依据的生命力
自从“国际鞋业”案判决以来,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即认为被告在一州的出现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必要条件的传统管辖权理论的相当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够对并未被发现出现在该州的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而又不违背宪法。
然而,传统理论也坚持,一个人在诉讼所在州的出现是该州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充分根据。这在过去是对的,甚至于就我们现在的“一般管辖权”而言,也是正确的。传统理论的这一观点延续下来了吗?许多律师、法官和学者认为没有。如果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检验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国际鞋业”一案和以其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将很难发现,在没有其他联系的情况下,仅仅由于被告在某州的短暂的逗留就要求其服从管辖在该州应诉的公正何在。在“国际鞋业”案之后,很多人认为,即使被告在该州逗留期间被合法传唤过,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确定要求被告在该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应诉是否公正。在Shaffer诉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际鞋业”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适用于被告在一州的财产被作为准对物诉讼的基础的案件。在该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对所有州法院管辖权的维持,必须依照在‘国际鞋业’案和其同类案件中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在Burnham诉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这一问题,即仅仅到过某州是否构成一般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如在Asahi案件中一样,最高法院又没能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
其中四名法官认为,在某州的出现仍然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对他们而言,“国际鞋业”一案仅适用于没有到过诉讼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认为,“国际鞋业”案的利益分析应当适用于该案,但建议在通常情况下,被告出现在某州足以构成管辖权。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绝接受任何一方的观点。于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样,在没有其他更多联系的情况下,关于被告的临时逗留是否构成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的问题,留给我们的仍是平分秋色的两种意见。
八、州法院对人管辖权的宪法性限制的总结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同意接受管辖权或对管辖权不持异议的被告行使管辖权。参加诉讼而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即构成不持异议。
一个法院能够对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个人行使管辖权。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辖权的充分连结点(诉讼请求与本州没有关系时)。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与本州有某种联系、在本州“经营业务”的法人行使管辖权。“经营业务”是否构成一般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取决于法人的业务行为是不是连续的、系统的和实质性的,以致能够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应诉是公正的。
一个法院也可以对某个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别管辖权,如果该个人或法人有意地与该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诉讼的起因正是产生于该联系,除非被告通过对所牵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够证明该管辖权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针对制造商提出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有意的联系可以通过“商业流通”理论建立,除那些适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观点的法院外。
一个法院可能不会对在本州属于被告的与诉讼请求无关的财产行使准对物诉讼管辖权,除非被告与该州之间存在能够支持对人诉讼管辖权的联系。
一个法院很可能能够对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过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辖权。
婢圭増妲�:閳剁姵鏋冮悮顔芥降閼奉亞鐓$純鎴欌偓浣烘樊閺咁喓鈧椒绔鹃弬鍦搼濡偓缁便垺鏆熼幑顔肩氨閿涘矁顕╅弰搴㈡拱閺傚洨灏炲鑼病閸欐垼銆冪憴浣稿灁閿涘本浼冮崰婊€缍旈懓锟�.閳垛€愁洤閺嬫粍鍋嶉弰顖欑稊閼板懍绗栨稉宥嗗厒閺堫剙閽╅崣鏉跨潔缁€鐑樻瀮閻氼喕淇婇幁锟�,閸欘垵浠堢化锟�鐎涳附婀虫い楣冩6娴滃牅浜掗崚鐘绘珟.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