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1-10-18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331次
摘 要: 摘要:本文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框架出发,探究直播带货疯狂生长的原因,并探讨直播带货的传播偏向与其内容呈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直播带货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得益于直播这一视频模式进入了镜子阶段;互联网让人们形成普遍连接的期待;直播间多感官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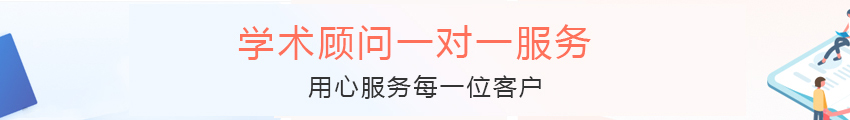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本文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框架出发,探究直播带货疯狂生长的原因,并探讨直播带货的传播偏向与其内容呈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直播带货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得益于直播这一视频模式进入了“镜子”阶段;互联网让人们形成普遍连接的期待;直播间多感官调动、刺激性符合和仪式化的媒介环境、直播间更具人性化和真实感的购物环境;直播带货具有空间偏向,重视世俗物质文化,因此其销售量高的产品多为日常用品、流行服饰和难以保存的商品等;直播带货所形成的前后台融合场景催生了男女气质混合的主播,并使得政府官员去严肃化而更具亲和力。但是,直播带货也给理性和道德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切勿让直播带货成为商家的不法之地,也不要让直播带货带来的只是一场虚假的泡沫狂欢。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直播带货;传播偏向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缘起
当下,直播带货正呈现出一种疯狂生长的态势,成为各大商家拉动网民消费的重要手段。在2020年的“618狂欢购物节”中,直播带货表现出不俗战绩,天猫“618”期间,有13个直播间累计成交过亿元,苏宁易购举办的“618超级秀”直播活动,在5个半小时里的观看人数破1.2亿,成交额突破50亿元[1]。
直播带货在电商平台已经具有了重要的角色地位。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直播带货这一新现象。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五方面。
1.对直播带货的微观情感动力机制分析:如强月新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了构成直播带货中互动仪式链的要素及其效果,并认为媒介逻辑、商业逻辑、政治逻辑共同作用于直播带货互动仪式链的动力机制[2]。
2.对直播带货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分析:如丁汉青运用媒介景观理论对朱广权和李佳琦合作的直播带货“小朱配琦”进行了个案解读,分析了主流媒体与网红共同生产的“购物剧”媒介景观[3]。
3.对直播带货乱象问题的研究:如夏令蓝等认为数据虚假繁荣、主播身份与行为性质界定模糊、消费者维权难、直播平台监管不力是当前“直播带货”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应当加快修订和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推动传统媒体转型,树立新媒体电商行业标杆,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与黑名单制度,从而推动“直播带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4];李向荣等认为直播带货的乱象表现在商品问题、虚假宣传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四个方面,直播带货乱象治理需平台、主播、监管部门三方共同发力[5]。
4.对直播带货批判性解读:如郑红娥认为直播带货是利用名人或明星效应,为博取眼球经济而实施的一种商品美学教育,其背后隐藏着资本对消费者灵魂的诱导、规训、征服等危机[6];闫玉刚等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直播带货所表现出来的狂欢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狂欢文化是一把双刃剑[7]。
5.主流媒体或领导干部如何更好利用主播带货的策略性研究:如陈婷认为领导干部“直播带货”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探索互联网营销的模式,从而不断提高“直播带货”的效益[8];陈静则分析了央视主播朱广权和网红主播李佳琦的首场直播带货中的传播策略[9]。
综上,目前的研究主要以直播带货的内容、法律规范、营销策略等方面为主,极少有从媒介环境学对直播带货进行解读。而媒介环境学突破了传统媒介研究中将人与媒介做主客体两分的局限,不再仅将媒介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物质来看待,而是认为人们并没有置身在人们使用的传播媒介之外,相反,人们就在其中[10]50,就如同在面对面交流时传播声音的媒介空气那样,人们并没有在空气之外,而是身处空气之中。并且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不再将媒介看作是中立的传播渠道,而是积极的行动者,媒介的物质结构与符号结构决定了什么内容能够被媒介传输、被传输的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框架是研究媒介如何为人们构建了感知环境、符号环境、社会环境,并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独特的传播偏向,从而对社会的文化、经济、心理各方面产生影响[10]42-57。
因此,本文将从媒介环境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出发,结合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莱文森、梅洛维兹、伊尼斯等人的理论,对直播带货从媒介技术方面进行解读。分析为何直播带货能够疯狂生长、直播带货与电视购物的差别、直播带货的传播偏向对其内容呈现和人的影响等问题,并对直播带货进行反思,以期能够促进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
二、技术与媒介环境的建构:直播带货疯狂生长的原因
(一)直播带货步入“镜子”阶段
按照莱文森描绘的“玩具-镜子-艺术”的技术演进三阶段的观点[11],直播已经进入镜子阶段。玩具阶段意味着技术仅仅被人们当作一种取乐的手段,人们对技术的认识还不全面,而镜子阶段意味着技术的功能被人们开发,并投入到了实际工作的运用,发挥实用功效。直播曾经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娱乐玩具,供人们在休闲之余观看球赛或者和主播聊天,尚处玩具阶段,而如今则进入了镜子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直播就展现出许多实用办公作用如直播采访、直播会议、直播课堂,而直播带货则展现了拉动经济的作用,正是借助进入了镜子阶段的直播技术,直播带货得以兴起。
(二)互联网让用户形成普遍连接的期待
直播带货的兴起得益于当今媒介化社会下人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连接的期待。理查德·林的研究认为,随着手机的广泛普及,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随时可以被联系到的责任[12]174,人们总是期待对方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被联系到,而人们自己也期待自己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被对方联系到。在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广泛普及的今天,人与人之间能够被随时联系的期待则变成了能够随时连接的期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认为对方能够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而实现相互的连接,不能连入互联网,就如同没有带手机一样,会给他人造成麻烦。从QQ到微信再到移动短视频,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在QQ中,每一个用户都有在线/离线的状态,在线状态下用户的头像是彩色的,而离线状态下用户的头像是灰色的,而在微信、移动短视频平台中,离线状态则不存在了,每一个用户都显示的是在线状态。离线状态意味着该用户当前无法联系,而在微信中,没有离线状态的存在则意味着每一个使用微信、移动短视频的人都能够被随时联系,能够随时与他人形成连接,使用微信、移动短视频就意味着人们相互间彼此期待对方永远在线,永远连接在一起,微信、移动短视频取消了离线状态符合了这种人们彼此间相互连接的期待。这种相互连接的期待也同样影响了直播带货,正是因为预设了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能够随时随地地连接到直播间,所以才会有人从事直播带货的行业,人们对彼此之间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的期待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主播们认为观众们上网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从事这项工作。在现实中的营销活动,具有更多的偶然性,因为其营销的活跃度常常取决于路过营销现场的人数,营销人员无法期待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营销地点,而在直播带货中,经由互联网的连接,主播可以期待观众及时地参与其中,观众也期待着主播准时开播和期待其他观众也观看直播,这种彼此相互连接期待推动了直播带货的发展。
(三)直播间的多感官深度参与
“直播带货”所塑造的感知环境是一个调动多种感官感知的环境。在直播间里,不仅有视觉感知、声觉感知,还有触觉感知。直播以视频的方式呈现,观众首先用眼睛关注视频中的带货主播和他们推荐的商品,调动视觉感知。带货主播同时以口语文字进行解说,并以夸张的语调刺激着观众的听觉,如李佳琦浮夸的呐喊:“买他、买他、买他。”调动听觉感知。同时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还会调动自己的手指去触摸屏幕,完成点击商品链接、滑动或放大屏幕、输入评论等触觉活动。由此可见“直播带货”是一个调动观众多种感官的“冷媒介”。“冷媒介”是麦克卢汉对媒介所做的一个分类,“冷媒介”在理解时需要动员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13]247,并深度卷入到媒介的使用过程中,用户与媒介互动性高。观众在观看直播带货的时候就已经被主播的各种行为与所展示的商品深深吸引,所以用户常常不假思索就在直播间购买那些不需要的商品。与电视购物相比,虽然电视也是一种冷媒介,也吸引观众参与其中,但是电视购物吸引的是观众精神的参与,因为观众只能够在大脑中与节目的主持人形成想象的互动,直播带货则由于可以发送实时信息而更具有互动性。电视购物往往在屏幕下方配有字幕,而直播带货则没有字幕,字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节目内容的清晰度,让观众能够花费较少注意力并清楚地知道节目当中人物所讲述的内容,而没有字幕的直播带货则需要观众集中注意力去聆听主播的介绍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商品的内容,没有字幕比有字幕的节目更“冷”,更吸引观众。此外,直播带货能吸引观众身体的参与,因为观众可以直接通过双手去点击屏幕中的按钮、链接以实现与主播的实时互动并直接购买商品,并且不用借助额外的媒介。
直播带货还塑造了一种与现实生活中感知他人在场方式相异的特殊环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感知一个人在场的方式是身体的出现,而在直播带货中,观众感知他人在场的方式则是语言的出现。观看直播是一种远程在场,这意味着此时和此地的分离,远程在场只需要语言在此时出现,而不用身体在此地出现。语言替代了缺场的身体,成为观众感知他人存在的符号。当观众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现在屏幕下方的弹幕和评论就表明了直播间有许多人正在观看。若是在现实空间中进行营销活动,人们往往会局限于当前实时在场的人数,并以此来判断现场营销的氛围,而与现场的营销活动不同,直播带货这一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的链接,让观众能够超越在场的人群,将不在场的其他观众与在场的主播和观众自身联系起来,让观众感觉到一种更加热闹的氛围,也与电视购物所形成的孤独氛围不同,直播带货让观众感到更具有群体感,形成一种群体的狂欢,当他们看到直播间中其他的观众都纷纷下单,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下单。
(四)带货主播刺激性的语言和理想性的身体展示
朗格将符号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符号”,一类是“象征性符号”。“一般性符号”是人类与动物共同享有的,一般性符号可以定义为发出信息,对某人或某个动物指示一种事物或一种状况。一般性符号有两种功能,一是表示某种状况的存在,二是刺激行为反应。而“象征性符号”则是人们将经验抽象化并存于大脑中的符号,是人类独有的符号,“象征性符号”又分为推理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前者指语言和数字等,其作用是帮助人们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真假,而表征性符号则是图片、建筑、音乐、表情等等,其作用是表达人们的内在情感,触发感性[10]418。
在直播带货中,一般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主导了直播带货的符号环境。一系列旨在刺激观众购买行为的口号,如李佳琦夸张式的呐喊:“买他、买他、买他”、“OMYGOD”,薇亚的秒杀迫胁式话语:“今天我只要到了2万件,没办法加,今天秒完就没了啊!”看到如此低的价格已经十分心动,还没反应过来,抢购就开始了。助理在一旁展示着领券的方法,薇娅大喊着“54321”。哪里还来得及权衡是否需要?“这种便宜不占岂不是吃亏?”[14]这一系列言辞都属于一般性符号的范畴,用以刺激观众的购买行为。在一系列一般性符号的刺激下,观众的动物性本能被激发,难免陷入“剁手”境地。
直播场景的设置、环境音乐、图片、商品、主播的仪态等则构成了直播带货中的表征性符号。不同色调的背景墙,能够体现出特定的情绪氛围,有的以红色背景为主色调,展现出一种喜庆氛围,而有的则以棕色、白色等背景为主色调,展现出一种理性、深邃的氛围,体现了主播和观众的高端内涵。并且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的仪表、举止也在向观众流露出他们对自己推销商品的情感,表演者可以停止表达,但无法停止流露[15]94,主播通过不停地情感流露,比语言表达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情体验。
同时,在直播带货中,身体成为重要的符号元素。身体在直播带货中成为“神话”,即巴尔特符号学理论中的神话符号。“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16]180意指即消费者在看到某个符号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某种境界。主播借助自己的身体展示着商品使用所带来的满足与快感,同时,直播间中观众的积极留言、认可主播表演的评论都激发着观众的想象,让观众能够自然地将商品和优质的生活与完美的形象联系起来。最容易被拉动消费的往往是食品、化妆品、箱包、服装等商品,这些商品大多和身体相关。最典型的是改造身体的塑形类商品,明星的广告和使用能引发大众的模仿,因为明星给受众建立了一个自己身体能够被满足或能够达到的理想标杆[17]。在神话的构建中,具有了消费特征和理性化形象的身体经过了两个层面的符号系统的交错,第一个符号层面上,身体的能指是生理学的器官,而所指是某一个人,在第二个符号层面上,前一个层次的所指成为能指,而所指则是主播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和物质欲望。通过这一系列的符号,使得直播带货能够改变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形成一种独特的消费文化。
(五)直播过程的仪式化呈现
在直播带货中,主播和观众之间也建立起一种具有仪式化意义的社会环境,“仪式是一种由多种行为构成的表达性、象征性活动,这些行为以固定的情景序列发生,而且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18]在直播带货中,这种固定的情节和行为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带货主播向观众推荐商品,然后带货主播借助自己的身体对商品进行展演,并进行仪式化的行为呈现,如推销乡村腊肉的主播以在山上云雾间吃饭来展示其美味和仙境[19];李佳琦以男性的身份在直播中试用多款女性口红,这是一种与人们传统性别经验相异的行为;其他的主播甚至在试用商品的过程中配上音乐,加以特殊的肢体动作,还有邀请明星嘉宾在现场为商品的推销助威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形成一种与日常销售不同的仪式化展演。之后,主播会以夸张的表情号召观众下单订购,观众就会像经历了一场仪式的洗礼一般,聚集在屏幕前的观众仿佛如同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容易被其他人的行为和语言所感染,导致群体极化,实行共同的购买行为。当一个商品推销结束后,主播又会进行下一个商品推销,并重复前面的行为序列,构建起一种仪式的传播。
美国的传播学者凯瑞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传播这一概念。凯瑞认为,传播本身应该被看作一次神圣的仪式活动,关注人们如何通过仪式中规则化的程序来描述并强化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20]当观众在直播中,无论是看到带货主播介绍商品的各种独特优点,还是试用商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满足感和舒适感,都能够强化观众对商品的好感度,更加认可商品可以带来的效用。通过一系列仪式化行为和仪式化传播,提高了观众对消费内容的体验,增强了观众对主播所推荐产品的消费态度,从而激发了观众的消费行为。
直播带货同时也建构了一条互动仪式链。强月新认为官员直播带货通过媒介技术实现观众和主播在直播间中的虚拟共同在场际遇、直播间所形成的互动和对话消费闭环、对消费需求的关注和情感的共同体验这四项要素形成了互动仪式链,使得观众和官员产生情感共鸣,迸发出情感能量,消费群体性符号,共享政府官员的道德感召[2]。若把视野放宽到除了官员之外的其他主播的带货,互动仪式链也同样适用。当观众看到直播间大量的在线观看人数时,就容易达成一种虚拟在场的共同体,共同关注着带货主播所推荐的商品,一系列的互动行为和带货主播的气氛渲染行为则强化相互间情感的共同体验,构建起互动仪式链。比如李佳琦在一次直播带货中,积极回应观众的需求,试用了几十支口红,这让观众们都纷纷担心他嘴唇的安全,强烈要求他不要再试用口红了,通过这样反复的互动,主播和观众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彼此间也更加认同。
相关论文推荐:谈直播与短视频分析媒介融合突破点
直播带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常社会购物模式发生了改变。在日常购物情境中,往往是导购员介绍商品,而试用商品的则是购买者,而在直播带货中,试用商品的却不再是购买者,而是起导购员作用的带货主播,主播通过将购买者在日常购物情境中的行为转换为自己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购买者在直播带货中的地位。
(六)人性化的直播带货复制了现实的购物环境
媒介技术人性化与非人性化的偏向理论来自保罗·莱文森。在莱文森看来,媒介总是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即使某种媒介存在着一系列缺点,后续出现的新媒介会逐渐将这种缺点进行补偿。直播带货相比于电视购物更具有人性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直播带货不需要借助其他媒介完成下单行动上。由于电视购物无法直接完成下单,需要借助手机、电话来完成,而当观众想买,但是电话、手机恰巧不在身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满足买东西的愿望,而通过直播带货则无须担心这一问题。其次还体现在其复制真实购物环境上。观众往往通过手机来观看直播带货,在直播带货中会浏览带货主播提供的商品,观众的浏览是一种近距离的浏览,与观众在超市中浏览商品的距离一样,也是一种近距离的浏览,这就让观众感到更加真实,从而直播带货找到了自己的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位指的是媒介与人类交流环境的某些方面达成了契合[21]184,直播带货与人们在购物时的近距离观赏商品这一环境达成了契合。而观众在看电视购物的时候,由于电视距离观众较远,所以观众与电视中推荐的商品距离也远,这与现实生活中观众浏览商品的情况截然相反。此外,在直播带货中,观众能够与带货主播进行沟通与交流,这与现实生活中购物的导购员交流的情景相似,而电视购物则无法让观众与其中的主持人交流。因此,直播带货更加真实地复制了现实生活的购物场景,正如莱文森所言,媒介所带来的环境更像是人性化的前技术情境,它并没有带来与真实世界越来越不同的传播环境[21]4。所以,人性化的直播带货比电视购物更能够吸引观众。——论文作者:黄洪珍,陈泰旭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