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发布时间:2021-05-08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356次
摘 要: [摘 要]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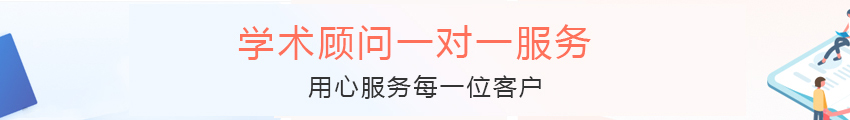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 要]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 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关键词] 赞米亚; 稻作; 农业边疆; 生态人类学; 物种间民族志
美国学者詹姆斯·C. 斯科特所著的《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的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作品,经过作者重新定义,赞米亚( Zomia) 的范围被限定为“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300 米以上的地方”[1]前言1 ,具体涵盖“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五国”的高地部分。按照这种划分方法,越南和贵州的山地,以及泰国清迈、云南景洪、掸邦首府景栋、老挝琅勃拉邦等名城周边的稻作区都包括在所谓“赞米亚”的范围内。长期以来,稻作都是这片“边陲世界”最为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它和以刀耕火种为代表的山地旱作农业一起,共同组成了本区域基本的人文景观。斯科特从中发现了更多的意义,两者分别作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代表,共同组成了包括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广大地区在内传统社会的根基: 稻作区是传统时代国家统治的核心地带,农民种植水稻,接受管辖,负担税收; 而山地民族则借助种植块茎作物和玉米等,试图逃避低地王国的统治,并不断向更深远的山地迁移,从而造成了人群分布的特定样态。不过,这种划分方式对于低地社会和山地社会的区别过于简单,很多民族显然在海拔 300 米上下都有分布,农业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片水热条件优越的区域得到充分发育,社会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出现了颇具区域特征的样态。
稻作是包括赞米亚地区在内的亚洲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它是如此日常,似乎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传统的土地制度、稻作生产的过程、稻米的流通情况等等在各地民族志作品中都会被提及①。但是长久以来,水稻农业的面目可能被层层的假设所遮蔽,宏观方面如稻作、灌溉体系与政权之间的关联,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与“内卷化”倾向之间的关系等,微观角度则如插秧、收获时人群间的互助、村落中对于水资源的分配等多为学界乐道,但是,不同族群利用所居住区域的水土资源从事生产的适应模式差异极大,基于东亚、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稻作生产模式得出的理论模型并不见得能够直接应用到所有以稻米生产作为主要生计模式的人群及社会之上。
在东南亚,古代王国多只统治与赞米亚相邻的河谷与平原地区,很多山地和丘陵地带极少会被某一强大政权持续控制,因此斯科特强调赞米亚区域“国家控制”与“无国家状态”一直处于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国的西南边疆古时多以土司的代理统治为主,东南亚缅族、泰族王国很多时候也并非是其全部领土上社会秩序的绝对主导力量。正如安德森所言,很多区域“缺少一种历史性的霸权势力”[2]5 。不管稻作是否能够构成国家存在的基础,但稻作生产方式与地域的政治秩序在很多时候肯定是存在紧密关联的。本文的讨论重点虽非在此,但把两者并置,方能与斯科特的结论形成对话,赞米亚地区的稻作生计中包含着突破斯科特论述的可能。
本文的田野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长短不同的田野考察经历,主要田野点包括缅甸掸邦第四特区、老挝琅勃拉邦及湄公河平原地区沙湾拿吉省、越南北部河江省等,国内则主要包括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德宏、普洱和贵州黔东南州等地。这些地区都属于斯科特所谓赞米亚高地中海拔相对较低的部分,其稻作呈现出多种样态。在这里,很多民族的农业生产都是水、旱兼营,两类生产方式并未像斯科特提供的模型一样处于彼此分离的世界,而在这多样的稻作生产模式背后是人类学家热衷讨论的人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学科史上“稻作文明”假说
一般说来,农业生产十分依赖稳定的水源,亚洲国家很早就开始修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以保障水稻生长期间的水分供应。为了建设灌溉系统必需把人群有效组织起来,这就成为一系列讨论的起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②和魏特夫的“水利与东方专制社会学说”[3]都曾在中国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两种理论都关注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设与国家的诞生及政权运行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主要在华北和华南展开的“水利社会”[4]99 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处在相关讨论的延长线上。
因创立文化生态学著称的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显然也受到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他同样强调为了满足粮食生产,需要集中人力建设水利设施,从而有了政权的兴起[5]。但是,从赞米亚区域的案例来看,即便种植水稻,也并非一定要组织大量人力去兴建大型灌溉工程,并进而步入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总产量—养活更多人口的循环中。比如,在老挝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沙湾拿吉省,灌溉渠至今仍很缺乏,而在中国的西双版纳,传统灌溉渠都不长,受益的村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早期生态人类学的假设在这个区域其实并不成立。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通过对印尼爪哇地区水稻生产的细致梳理,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命题[6],他观察到爪哇农民倾向不断增加水稻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期获得更高的产量。但是在养活更多人口的同时,稻作生产实际陷入一种闭合式的循环中,劳动的密集投入无法带来产出的同比例增长或者说仅能保证收入维持在一个水平上不下降①。农业内卷化的现象与传统稻作民族的文化 - 政治体系密切相关,稠密的人口与对水稻高产的要求互为因果并彼此强化。格尔茨的研究在东南亚、印度等主要产稻国的相关研究中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应,在中国史研究中,黄宗智较多使用“内卷化”概念,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②进行验证。
水利社会、内卷化的话题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亚洲的平原稻作区很可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来,有关水利社会的讨论更加关注人群的组织形式,而“内卷化”的着重点则是经济效益的测算,但是,正是在那些人群高度组织起来建成发达的灌溉设施的地区,更有可能出现所谓 “农业内卷化”③现象。就东亚来看,中国的江南和华南的稻作很早就迈上集约发展的道路④,同时这些富饶的稻作区往往也是国家税负的主要来源地。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存在,比如云南西南的傣族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稻作基本上没有什么田间管理,土司政权和王朝政府基本不按照土地和粮食产量征税。在粮食供应总体充裕⑤的赞米亚区域,稻米生产并不特别依赖人工灌溉设施,也未出现农业内卷化的倾向,以上研究显然忽视了稻作生产内部的巨大差异,赞米亚地区稻作的特殊性蕴含着挑战传统学界对于农业社会系列推断的可能。
斯科特在对赞米亚区域的研究中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农作物成为检验人群关系的一项标志: 稻作被认为是服从于政权并有利于征收赋税的生产方式,与山地民族从事块茎类逃避作物种植的所谓“逃离的文化与农业”相对。他强调“一个从事块根和块茎作物耕作的社会比谷物种植者更分散和更少合作,因而其社会结构更有能力抵制被统合,以及抵制等级结构和从属关系”,与之相对的“水稻国家需要并且培育了清晰的灌溉水稻景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口集中”[1]216 - 269 。斯科特的系列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近年来的回应和对话在中国学界也已有很多⑥。不过,斯科特一味“强调国家与定居农业的永久结合”,可能低估了稻作农业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以此作为立论基础可能是有问题的。
经过最近数十年的迅猛发展,很多地区的稻作农业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无论是黔东南的侗族还是湄公河谷地的老龙人其传统的稻作生产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通过田野考察,对稻米与块根作物的培植问题进行梳理,仍然具备与学科史上影响深远的假设和研究范式进行对话的条件。
二、灌溉农业与旱地农业: 赞米亚地区粮食生产中的异和同
( 一) 水稻与块根作物
斯科特对赞米亚地区的讨论基本出发点之一是耕作方式与人群所处政治生态存在对应关系: 种植水稻的人群听命于政府,定居并按时用收获物来完税,而栽种块根作物的人们总是不甘心接受控制,试图移居更远的山林。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果真如此明显吗? 唐代诗人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是中国送别诗中的名篇,诗中对于地方情态有很多有趣描述。当时的梓州地区( 今四川三台) 是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地方,所谓“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后一句表明当地生活的巴人似乎以种植芋头为生,因为田产方面的纠葛,他们需要政府做出判决。这表明早在唐代,生产块根作物的土地已经处于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了,种植芋头显然不能简单地看成所谓的逃离农业。不管巴人是否曾以芋头的种植来对抗古代国家政权,但毫无疑问,此时的他们是在国家税负体系内实践着块根作物的生产。
相关知识推荐:cscd农业类期刊有哪些
禾本科粮食作物的生长往往离不开充足的光照,在开阔的田地上生长最佳,而很多块茎作物更适合生长在林下,有时需要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人们选择种植哪种作物首先考虑的是农地所处的自然环境,可能并不总是为了隐蔽和逃离控制。一般说来,东亚和南亚平原地带的稻作严格按照月令行事,播种和收割时间往往都很集中。连片种植的水稻几乎同时成熟,从而构成壮丽的农业生产景观。与之相对,块茎作物的收获季节性确实不强,一些物种成熟期前后植株表面几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采收时间可以不那么急迫,斯科特由此推断这种属性便于人们躲避税收。对于这个说法,田野调查中也多有反例发现: 在大部分地方,村庄种植的块根作物无论是芋头、甘薯还是较晚引入的木薯其实也都会有相对固定的收获期。
另外,从食物的结构看,斯科特提到的所谓逃避农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也是需要检讨的。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早先人类学热带海岛丛林民族志所描述的景象移植到了赞米亚地区的山地中。块根作物确实可以和各种旱地作物、稻米一样充当食物,但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不同种类的食物往往存在等级差异,比如山地中生活的越南河江省蒙人经常羞于承认自己家以玉米或荞麦为主食,而不少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老挝 Bru 人也认为大米才是最好的粮食。确实,山地民族主要经营的是旱地农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一般说来这种耕作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在一片土地上同时种植多种作物,但大部分族群在种类繁多的粮食品种中并不特别热衷块根类作物,不仅现在如此,赞米亚区域在历史上其实也很少有像太平洋热带海岛上那样依赖芋头和薯蓣等块根作物的族群。何况,山地民族和谷地民族间存在着频繁而持久的接触,稻米基本上是整个区域都认可的主要食粮,没有稻田的民族多会想方设法交换或者购买大米食用。另外,一些山地族群其实更多把块根作物视为自然馈赠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只是获取自然生长的植株,只不过操作的时候并不会刻意挖尽,仍留下一部分任其继续繁衍,短期内其生长的位置并不会移动,而这种情况斯科特基本上也没有论及。
( 二) 稻作与刀耕火种: 低纬度地区农业的殊途同归
在通行的研究范式下,以刀耕火种为标志的旱作农业与水田稻作农业一般会被截然分开,斯科特也因此推定对应的游动和定居代表本区域文化的两种类型。山地的旱作农业和谷地的灌溉农业表面上看确实存在明显差异,这是居住地的水土资源差异造成的,但同处在更大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两种生产方式其实很难截然分开,它们拥有共同的农作思想,共享很多的知识和技能,彼此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经过多年研究,学界基本已经确认刀耕火种并非采集、狩猎生活“进化”到定居农业前的过渡类型,人类学家相信这是一种可以高效获取多种食物的低人力投入的农业经营方式[7]: 人们砍伐地表的树木和杂草,借助火焰清除覆盖的植被,种子播种后一直到收获,期间基本没有规律性的田间管理活动。连续种植数年后的田地会被休耕抛荒,依靠自然之力进行恢复。村民转向临近的其他地块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自然资源出现衰退的情况,村寨还会进行整体搬迁,到另一区域耕作与生活,这也就是所谓的游耕。相对而言,从事水稻种植的民族多是连续耕种,基本上很少迁移,研究者一般称之为定耕。但是,在赞米亚地区,这两种农业生产类型保持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彼此并没有绝对的差异。在传统时代的西双版纳,由于地多人少,土地为村寨共有,总会有很多耕地处于休耕期,除了轮歇时间较长外,一个家庭耕种的田地经常会发生变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类似于游耕。另外,在中国云南和临近的老挝北部,很多族群虽然经营的是刀耕火种的旱作农业,但同样践行佛教信仰,佛寺建筑一旦固定,游动耕作的范围自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迁徙的频率也大为降低。由此可知,两种耕作体系的差异在实际操作中是会不断消弭的。
水稻的生长十分依赖水源,东亚和南亚的稻作区很早就建立起了完善的灌溉系统。灌溉面积增加固然会明显提高粮食产量,但这种人工修建的水利设施一旦失效,也会给当地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鉴于灌溉设施的建造和维护会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组织与动员,就这个层面而言,斯科特所谓“国家控制的定居农业”在东南亚低地是存在的。但是,这并非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选择,传统时代西双版纳和泰国北部都只有十分简易的沟渠,每条灌溉渠受益的村庄数量都不多,修筑灌溉系统的规模与跟东亚稻作区差距极大。有趣的是,当傣泐人迁入泰东北南府后,反而以善于修治灌溉渠在周围的傣阮人中名声大振,被视为积极建设水利设施的典范①。对老挝中南部湄公河谷地的田野调查也发现,这些区域多是依靠季节性的自然降雨来种植水稻,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处于休耕状态,甚至是清迈这样人口密集的区域中心,仍然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水稻一年一熟的农业生产节奏。按照萨林斯的说法,赞米亚区域的稻作或许从“资源低度利用”[8]49 角度来理解更为恰当。此类农业生产活动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来组织,社区运转的核心更多在于村寨内部,所以稻作与政治集权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紧密的关联其实仍需具体讨论。——论文作者:张海超 张 晗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