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发布时间:2017-12-02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233次
摘 要: 现在很多思想都是在儒家道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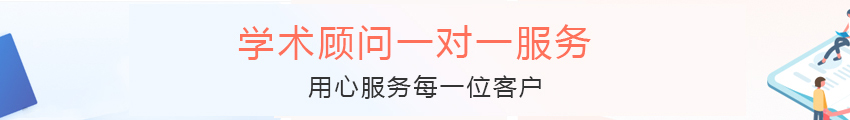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现在很多思想都是在儒家道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省传统儒学,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其理论渊源,通过中、印、西之比较而进行批判,分明壁垒,吸纳佛学的思辨体系或西学某些概念,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凸显儒学特质之优长及其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试图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关键词:儒家道统,中国思想史,"五四"时期

研究儒家道统,对当前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具有一定的理论、现实意义。“五四”时期,熊十力等人有感于梁启超等人游欧亲历,以及国内反传统思潮,其表现出强烈的儒家道统接续意识,通过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厘清其发展状况,提炼其理论特征是当前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以往学界以熊、牟一系心性道统论总概现代儒家道统论,没有将“五四”时期以“礼乐”及学术传统为道统之传的思想列入其中进行研究。梳理、提炼、解析“五四”时期儒家道统的接续是必要的。兹整体解读、学理分析之,以期为此域之研究聊尽绵薄之力。
一、背景:人文主义之回归
辛亥革命之后,皇权政统瓦崩于革命,无皮之毛的道统的坍塌亦已在劫难逃。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科学犹如一把双刃剑,其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让人痛感于心。同时,西方现代两大哲学、文化思潮——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分立与角逐,深刻影响着国内思想界。一战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高涨以及梁启超一行欧游之旅的所见和所感迎来了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之回归。在此历史背景下,儒家道统的现代接续应运而生。
武昌一役,中国政局焕然为之一变:自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君主之位被代之以中华民国共和政府大总统之职。延续两千年之久的皇权政统就此瓦崩,中国从此踏上了重建现代政统的艰难的民主共和之旅;护国一役,民国政局猝然为之小变:基本维持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局的北洋新军领袖袁世凯的败亡,使得北洋各军阀割据时代猝然到来,武夫当国,群雄逐鹿。
为让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共和的武昌、护国之役,并未能打出一个趋于理想的新国家、新秩序,梁启超所作的一段沉痛反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人的心声:“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有希望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1然儒家道统与皇权政统休戚与共,同命相连。陈寅恪对此洞若观火,亦痛心疾首: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2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皮、毛尽去,社会规范、道德秩序又何以为继?现代政统、道统之构建岂是朝夕之间、一日之寒所能成就!陈寅恪之悲绝即在于此。希望、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巨大落差,巨大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3皮毛相随和这“巨大落差”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鉴于时人“伦理的觉悟 ,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4的觉悟,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妄图藉播扬张大道统之力,以恢复传统皇权政统而兴起之尊孔复古的倒行逆施,以北京大学为基地,《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动一场揭橥“民主”、“科学”旗帜的、旨在彻底批判传统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民族性成为一种被批判的概念,成了极其迂阔、极不入时的东西,无皮之毛的道统坍塌的命运已在劫难逃。“五四”之后,宣傳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新文化运动之主流。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流派层出,精彩纷呈。思潮迭起,此起彼伏。相与争锋,角逐激烈。然自其内容和立足点观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思想阵营,即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又言实证主义,其成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法国的孔德实证主义,之后有英国之穆勒和斯宾塞承之。实证主义强调知识的实证性和为学的实证精神,认为唯有经历实证的知识或经验、现象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
而对于经验或者现象世界背后之本体的研究采取搁置一旁的态度,认为这是神学或形而上学所解决的问题。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德国、奥地利之马赫主义、美国之实用主义出。马赫主义,又名经验批判主义,它基于实证主义而将世界尽数归结为感性的、经验的,认为经验、现象之外不存在任何本质、实在。实用主义基于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而视经验为世界存在之基础,认为经验之外无物也。同时,受叔本华之意志主义和柏格森之生命哲学的影响,它将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行动”及其“效果”,把“经验”、“现象”、“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知识”则被视为“行动的工具”,而“真理”被降格为“效用”,从而宣扬有用即是真理的主张。杜威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大家,他将实用主义运用于社会、政治、道德、教育等各个领域。
强调经验方法的应用。并认为一切知识均是人们为应付环境而创造的工具,真理就是人造的工具,从而肯定人的思维即是工具性的;与之相对应,人本主义思潮,即非理性主义思潮,其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之叔本华之意志主义,后尼采的权利意志主义承之,他们认为,人的生存意志,即生存的情感和欲望是本体,是世界之本源和动力,即世界源于这种非理性的自我生存意志。尼采则将此本体提高为权利意志。柏格森之生命哲学则总结前学,以包涵生存意志和权利意志以及无意志在内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为世界之本原。他强调,经验和理性不能认识生命冲动,唯乞之于非理性的本能、直觉来领悟之。
当时国内倡导实证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之哲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注重实验科学及其逻辑、方法论,而拒绝经验现象之外的、即形而上学的研究和讨论,斥形而上学为“玄学鬼”的思想文化思潮就是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或反形而上学之主流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自严复系统地引进孔德、穆勒之实证主义思想以来,以“实测内籀”之学为主的近代科学方法广为国内学人所接受和推崇。王国维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实证主义倾向,与严复一样,他并未坚持西方实证主义坚定的反形而上学之思想立场。对此,他还颇为困惑地指出: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随着西方实证主义之一分支——实用主义的出现,并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作为传入者和中国实用主义之代表人物的胡适则连同其反形而上学倾向一同引进,而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搁置不理。他一方面指出,人之认识仅限于现象和经验的领域,另一方面则将清代朴学等传统方法论与近代科学方法相沟通,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著名方法论。与此同时,丁文江、王星拱将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马赫主义引入中国,并在“五四”时期的人生观论战中发挥其思想效用。
1920年3月,梁启超、张君劢师徒一行七人结束其为期一年有余的欧洲之旅。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展现出来的现代科学、文明之恶的一面让其心有余悸,幡然有感。“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2对此,来自西方的饱西学之士辜鸿铭亦有此先明,他说,“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3游歐归国的梁启超则不无感叹地宣布:“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
因此,“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他还鼓励青年并作如下要求,“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6梁启超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汇他国文化新鲜、优长之因素,以成充满活力之中国现代文化,以服务于全人类。总之,这些人认为,颇具人文主义特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可以并应该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世界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按照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在“五四时期”主要思潮中,这种坚持接续儒家道统的思潮,自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特别是在经历过曲折、起伏后,其现实意义更为突出。
二、内容: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
在“五四”时期人文主义回归之时代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人曾致力于通过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他们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接续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
接续是指对儒家道统在承继基础上予以新时代之创发,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异构是指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此来彰显和接续儒家道统。异构是接续现代儒家道统之重要一环。如,二十世纪初风靡中国的佛学复兴思潮给予法相唯识学以复兴和光大的契机,法相唯识学建立在因明的基础上,其“长于名相分析且注重因明逻辑”,7其颇具缜密的、丰富的逻辑性和理论性的理性思辨体系。章太炎提出:“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8理由是“盖近代学术,渐趣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
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1熊十力则吸纳法相唯识学缜密的思辨体系,旨在一改宋明儒家道统论随处点说、语录式的表现形式,以成系统之现代儒家道统论。他承接宋明儒家心学道统论,“集全力于建设纯粹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以‘内圣’——‘求心’为方向的”。2其所构建的新唯识论体系,“将体证的知识和严格的客观分析方法结合起来”,3这得力于熊十力所就学的南京内学院欧阳院长4的教导,其以逻辑性、理论性、体系化而见长于宋明儒学,这从其“体用不二”说、“翕辟成变”说可见一斑。也是从批判佛学、西方哲学入手,熊十力着力于接续现代儒家道统。
他“以体用不二立宗”,内批印度佛学之“分别性相”,外伐西方哲学之本体与现象的割裂之弊,意在于维护传统儒家之道的一以贯之。其“体用不二”说廓清了黑格尔等西方哲学之本体与现象的割裂,以及佛学之“体用两橛”、宋明理学之“静体动用”之弊,构建具有强健功能的“翕辟成变”说。他揭示出“辟主翕从”,即“心主物从”。强调心对物的主宰,赋予宇宙之道以社会伦理的意义。其本体论、宇宙论均服务于接续与改造宋明儒家心学道统论的思想成果,即“本心”、“性智”。这是熊十力对传统儒家思孟一派心性道统论的接续和光大。
有学者说,“它既承接发扬了宋明理学的‘内圣’心性理论,又在现代条件下,完成了康、谭、章的哲学事业,即再次融会儒、佛以对付西学的挑战,强调西学(科学、认识、‘量智’)虽可辅助中学(‘性智’、本体),但低于中学。在表面上,他是在批判佛学,实质上却是针对西学的。所以它才是现代条件下发展了的宋明理学。”5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十力批佛、伐西之举,并非持传统儒学与印度佛学、西方哲学一争高下,而是立足于现代,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通过对佛学、道家以及西学,甚至传统儒学的汲取与吸取,以接续现代儒家道统。
正如有论者说,“熊十力批判佛学的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儒学传统,就必须从整体上肯定儒家价值系统和人生态度的基本点,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和积极作用”。6对此,贺麟评价指出,熊十力“得朱、陆精意融会儒释,自造新唯识论。对陆、王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的本体,且本翕辟之说,而发展设施为宇宙论,用性智实证以发挥陆之反省本心,王之致良知。……兹仅拟就其哲学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7可见,熊十力的思想成果是对陆王心学道统论的现代接续和发展。
又如,梁漱溟弃佛从儒,以接续和归复传统儒家道统,旨在为中国文化寻出一条现代的路。借鉴西方人本主义概念,梁漱溟以“意欲”定论文化。通过对中、印、西文化的比较,接续传统儒家道统之优长。他毕生追寻着两个问题的解答,“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8这是时人所共同面对的、颇受困扰的问题。
怀揣着对佛学的钟爱,却为被时人所不齿的孔子鸣不平。梁漱溟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9这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儒者气概。他还说,“孔子的态度是最平正实在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是需要的,佛家的态度则于国家于社会无补。因此,虽然我自己内心倾向佛家,却不愿意社会上流行这种念佛的风气”。10立定“以儒家精神济世,以佛家精神安身”的立世处事原则,梁漱溟转向儒家。他说,“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
梁漱溟提出,对于孔子之道的接续和归复是在为中国寻出一条现代的路。儒家道统之外王事功一脉也是儒家道统之根本所在,此期,接续和归复儒家道统周、孔外王之道是当务之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提出“三路向”说。他强调,“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形式肯定了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2他借鉴柏格森之生命意志,创发“意欲”范畴以定论民族文化,通过对中、印、西文化之比较,凸显传统儒家道统。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意欲向前”,注重物质,可引导出民主、科学来。“
意欲反身向后”,摆脱现实生活,体现了宗教性质。而中国文化之“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融合天人,自求满足,是一种伦理文化。鉴于物质、精神二者的综合考虑,强调、突出符合“生命本性”的中国文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梁漱溟将孔子学说作为形而上学来理解。他指出,“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孔子说的‘一以贯之’恐怕即在此形而上学的一点意思。”4“一以贯之”的孔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德伦理学说、社会政治学说,浑然整合于以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就这样,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道统论是以内仁外礼为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与政治形而上学的复合体系。
二十年代初,张君劢就意识到道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对宋明儒学的提倡和更新。进而指出:“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5自“理论”观之,张君劢论“新宋学”,实为抨击汉学之故。对于为陈独秀、胡适等西化派学者所标榜的体现“科学精神”之汉学,即清代朴学,张君劢斥之为支离破碎的饾饤之学。他认为,义理之学并非一味空疏的,而是“皆有至理存乎其中”,6其求严格的“修省功夫”亦是实践之学。因此,他说:“吾国思想界中孔孟之垂训,宋明之理学,自为吾国文化之至宝,以其指示吾人以行己立身与待人接物之方。伸言之,指示吾人以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也。”7自“实际论”而观之,“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
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图饱暖,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8在他看来,时下之人毫无信仰,不知责任。世道人心如此,国家危矣!以国计民生言之,当“知礼节”而后“衣食足”,不可否认道的倡扬对于经济、政治的作用。他进而指出,“昔之儒家有学禅之实,而不欲居禅之名。吾则以为柏氏倭氏言有与理学足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摈弃之。
……试以美国煤油大王之资财,畀之今之军阀与政府,则财政能整理乎?尽人而知其不能矣。何也?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故也。又试倾英伦、法兰西、日本三国家银行之资财以畀之今之军阀与政府,政治其清明乎?亦尽人而知其不能矣。何也?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故也。……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9而西人有类于宋明儒家之道的“柏氏倭氏言”,因“知礼节”且“知荣辱”,故“衣食足”且“仓廪实”。中国“财政”之“整理”与“政治”之“清明”正有赖于对宋学的倡扬。
二十年代出版的《人生哲学》是冯友兰比较中西文化的代表作,其原书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虽然他没有象梁漱溟那样,将中、西、印三种文化归结为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但是,他在书中把东、西方有关人生哲学的思想以“天”、“人”、“损”、“益”来概论之,归纳为“损道”、“中道”、“益道”。他认为,儒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人生哲学为天人和谐、损益适当的“中道”。虽此说无中西对立之比较,但其中彰显儒家之道、接续儒家道统的意识显而易见。
三、评价: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五四”时期,熊十力等新儒家在求异中凸显儒家道统,通过反省传统,甚至批判传统道统论来接续儒家道统。这与“五四”以前康有为、陈焕章等发起的、旨在建树孔学宗教1之尊孔、祭孔复古思潮迥然不同,后者是一味崇古、泥古、滯古,未能科学、客观地看待传统。前者则是基于传统的融汇中西、发明新义。而熊十力等人异构现代儒家道统的理论努力则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此期儒家道統论虽与晚清体用之论大相意趣,不再以体用相分的方式对待西学。他们认为,西学之体用皆可出自于儒学传统,这并未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熊十力认为,“六经广大,无所不包通。科学思想,民治思想,六经皆已启其端绪。如符号推理,及辩证法,《大易》发明最早。树其宏规。六经言德治或礼治,实超过西洋民治思想甚远……如《周官》法度,亦含有民治之法制,但精神迥别。科学方法,六经虽未及详,而孔子已注重实测术,则不容否认”。2也就是说,西方之科学、民主,在六经中都已启其端绪。
梁漱溟认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3科学、民主可以整套接受,但西方实用主义、理智主义的态度要“根本改过”。有学者评价说,“梁漱溟认为,较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那么它自然能够包容西方文化的发展成果于自身之中,尽管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是矛盾百出的。熊十力试图把中国文化诠释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弹性结构,以证明它足可作为‘吸收外化之基础’”。4对此,贺麟如此评价梁漱溟,他说,“不用讳言,他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他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
然而他却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他也没有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的地方”。同样,在钱穆眼里,中国传统政治是美好的,是瑜可遮瑕的。他说,“中国政治,自秦汉以下,本有一种理性为之指导。法度纪纲粗建,无豪强之兼并,无世胄僧侣之专政,教育选举考试与统治权常有密切之联系,不断吸收社会俊秀分子,公开参政,使其新陈代谢,政府与民众即以此为连锁”。6他只论传统政治之优长,对于中国历史上“专制”、“封建”也不予认同。他得出结论:“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
冯友兰否定全盘西化,他指出,“如照‘全盘西化’的逻辑推下去,则中国人应一律崇奉耶稣教,长袍马褂也不能穿了,须改穿西装;馒头大饼也不能吃了,需改吃面包”。8他对民主、科学的主张是基于“清末诸人的主张”——“中体西用”的。他指出,“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说:清末诸人的主张是‘正’,‘五四时代’是‘反’。我们今日的主张是‘合’。‘合’虽然有点像‘正’,然而他已包有了‘反’在内。”1引进西学当以中国“五常”道德为本体。“照中国传统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天不变,道亦不变’,对于‘常’仍是可说底。”2五常是体,是道。显然,冯友兰“仍然是从‘圣人最宜于作王’的角度说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可以说,冯友兰重弹清末“中体西用”的老调子,他对于传统的态度近于晚清“维护传统和抵御西方文明的‘士绅’心态。”
此期无论在论述架构形式上,或是在对于道之本体的重构上,熊、梁二位均没有吸纳西学之架构、逻辑、知性及概念,以补传统道统论之不足,没有能够以现代哲学体系架构、概念来重构现代道统论。正如有学者所说,“熊、梁属于前现代,道德人格与学问知识仍是混而未分,要求同一。”5换言之,此期对传统儒家道统论的接续继承有余而阐发不足,具有浓郁的复古特色。这主要由于熊、梁等中学饱学之士对西学的生疏或曲解,以及缺少深厚的、严格的西学教育。因此,熊十力等人以求异的方式重构现代儒家道统,在比较、批判中凸显儒家道统,其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学衡》,第64期。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第389页。
4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1 王国维:《自序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 梁啟超:《在中国公学演说》,《申报》,1920年3月10日。
3 包恒新:《辜鸿铭与<怪味嬉皮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4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演说》,《申报》,1920年3月10日。
相关阅读:政治论文论述儒家思想对当下文学有何影响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