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8-01-0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271次
摘 要: 明末清初,变化巨大,士人群体的生存环境遭受了巨大打击,生存困境与遗民情结构成他们共有的生命体验。改朝换代之际的诗人感慨身世,怀念故国,文人复杂幽微的心绪,与其内外交困的人生境况互相交错,体现在清初诗人对生死两难、出处行藏、人伦范式与时代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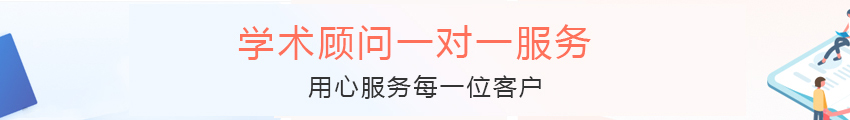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明末清初,变化巨大,士人群体的生存环境遭受了巨大打击,生存困境与遗民情结构成他们共有的生命体验。改朝换代之际的诗人感慨身世,怀念故国,文人复杂幽微的心绪,与其内外交困的人生境况互相交错,体现在清初诗人对生死两难、出处行藏、人伦范式与时代困局等问题的文化反思和诗学主题之中。而儒道“逸”的思想和佛教禅宗“空”的境界,当是这种遗民情结主要的文化缘由。
关键词:清初诗人,遗民情结,诗作主题,文化根源

明季之亡天下,社会动荡,政局多变,士大夫面临道统断裂、文化失语的困厄局面,失落感空前,其文学创作亦以抒写忧愤愁苦之情见长。清初诗人常常书写其对时局变换和自身困境的深刻体验,表现得哀感顽艳,甚至触及其进退两难中的幽微心绪。他们希求平衡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写作和反思,也是乱世文人为寻觅人生出路、实现自身价值所作出的努力。
一、遗民诗人与遗民情结
“遗民”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类,前者是指改朝换代之后幸存下来的人,不带任何政治与感情色彩;后者指改朝换代之后不肯出仕新朝或有强烈怀念前朝意识的人,它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这个定义的内涵是遗民问题探讨的重点[1]6-7。清初语境下,遗民的所指是明清易代后义不仕清的文人。遗民情结主要指遗民士人的群体性情感心理,比如黍离麦秀之悲、身世浮沉之叹和宗国兴亡之思等。但这些情感并非为“遗民”群体所特有,面对家国沦亡的惊天之变,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很难无动于衷,“变节”者亦有无可避免、难以消解的遗民情结。
明清易祚,士人处境艰难,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故国之思导致他们对现实不满,而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层面的严酷现实,亦加深了其内心的郁郁之气和黍离之悲。明亡之殇,民生之苦,时事之叹等相互交织,与其宏图难展、清冷难耐、鸥盟难违等多重情感汇集一处,构筑成那个年代文人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世界。此时的诗作主题涵盖深广,主要是感慨身世与怀念故国两类。
(一)感慨身世
神州陆沉,士人陷入了“逐客已无家”[2]的窘境。清代立国之初的政治举措,压制了东南地区的反清情绪,却也使士人阶层噤若寒蝉;遗民诗人“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分际、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3]5极为明显。外界种种纷繁折射入人心,加重了这种心灵漂泊的凄惶之感。“游”是明遗民的生存常态,包括游离、云游、交游等;但转徙江湖之苦与漂泊无依之感,每每充斥于其笔尖心上。
抗清失敗,恢复无望,部分遗民选择远离中土东渡海外。朱舜水《漫兴》诗“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4]17,感慨独在异乡、知交零落的悲戚;而其《避地日本感赋》中“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4]18句,情感更为复杂——服饰是制度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彰显本朝正统,改朝换代往往伴随改正朔易服色,清廷“易服”之举中断了华夏衣冠的发展轨迹,而日本和服从形式上更接近于华夏传统服饰,且日本向来深受中原文明影响,在日本的所见所感或许会让朱舜水稍感安慰;遗民依旧难忘故国,但在破国之悲、飘零之伤外,却有在文化意义上“存灭国”、“继绝世”的意蕴。“剃发易服”的屈辱让清初“逃禅”者激增,要求死后以僧服入殓者亦不止吴伟业一人;东渡遗民则在台湾岛上传承着华夏衣冠和儒家道统。永历年间东渡台湾的宁靖王朱术桂,在郑氏降清后写下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几根发。今日事已毕,祖宗应容纳。”而后他从容自尽,因为“自以明室宗亲,义不可辱”[5],纵然半生漂泊,但发式代表着文化认同与个人尊严,不可剃发受辱。
(二)怀念故国
清初江南屡遭涂炭,士人多有黍离麦秀之悲和世事变幻之痛。冯班诗句“莫道陆居原是屋,如今平地有风波”[4]19在故国之思外,凸显了面对时局莫测的无力感。谈迁的“今日广陵思往事,十年前亦号承平”[4]12诗句,则以极沉痛的语调感慨昔盛今衰之景,叹息扬州因战乱再度沦为“芜城”;其《渡江》诗则反映了遗民诗人对历史的审视,“击楫空闻多慷慨,投戈毕竟为沉酣”和“闻道佛狸曾驻马,岂因佳味有黄柑”[4]11两联,痛斥福王政权的腐朽,是对南明败亡原因的深刻反思。
宗国破灭之悲与昔盛今衰之感,及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和思考,是为明季文人所共有,即使在新朝入仕或应举者,“其故国之思未泯,民族的隔阂未除,所咏的诗作大多流露出故国故君之思,或借故迹以凭吊,或假往事而伤感,极少对新朝事物描写与歌颂,甚至指名直斥,不稍隐晦。”[6]不少仕清文人宦途并不如意,他们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亦会加强其对“遗民”生存价值与文化符号的认同,如钱谦益的“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7]73,明显含有对桂王的悲悼;而吴伟业的“辜负故园梅树好,南枝开放北枝寒”[8]496,暗含扬州梅花岭与史可法故事。吴梅村常常书写由历史人物或史实引发的时事之感,以及山水行途中生发的悲凉之情,“浮生所欠只一死”[8]398诗句,便是其登临八公山触景伤情后迸发出的强烈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故国之思中含有抗清题材,“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洪亮吉《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赴后继。”[9]遗民诗人关注“恢复”者首推傅山,他多次参与反清斗争,如诗句“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4]27对恢复讯息的及时回馈,在清初诗作中几乎俯拾皆是,诗人或热切盼望,或悲慨叹息。当时局战事“偶传消息好”时,对故国有所怀恋的文人几乎无视自身所处环境的恶劣,纷纷留下乐见恢复的诗篇,“喜慰一登临”[10]300。对于南明抗清的局部胜利,不仅遗民欢欣鼓舞,失节文人也多有庆贺,如钱谦益的“廿年薪胆心犹在”[7]66;“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7]69等诗句。直到康熙年间,天下承平日久,这些情绪才逐渐从诗作中褪去。
二、生存困境与诗学主题
明清易祚,士人的生存方式虽有异,却都难以超脱痛苦,外界环境中,人生道路、人伦困境乃至情势变化使他们进退维谷,内心世界的超越因而变得极为重要。他们逐渐将关注目光从向外投射转向了内省,希冀在方寸之间寻求一处桃源;但无可避免的生存困境,却使清初诗人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
(一)生死两难
对于死亡话题,遗民诗作隐含忠烈之气,诗歌语境大多歌咏节烈之士与感叹朋友亡故;而失节文人群体对此亦触动颇深,悲叹自己未能从死,痛悔之情产生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相对而言,遗民诗人更多地表现出对死亡的超脱与对舍生取义的赞同,及因志同道合者去世而引发的物伤其类的悲慨;而贰臣诗人从自身经历出发,往往对未死且失节的遗憾悔恨居多。
如吴梅村涉及生死问题的诗作数量多,且艺术成就非凡,虽不排除“自饰”,但悲痛愧悔之情早已溢于言表,如“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8]260,“浮生所欠只一死”[8]398,“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8]531等。邓汉仪选择苟且偷生,“千古艰难惟一死”[10]1785写出了他面对死亡选择的伤心彷徨。钱谦益“忍看末运三辰促,苦恨孤臣一死迟”[7]66亦为应死却未死而后悔。好生恶死原是人之本性,但在道德伦理的话语体系下,个人的选择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舆论压力,失节者对死亡题材的关注、书写和反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遗民诗作提及死亡,往往不出七尺为轻、痛失知音两大主题之外。阎尔梅《绝贼臣胡谦光》诗的“生死非我虞,但虞辱此身”[4]22句,反映的生死观在遗民诗人中颇具代表性。黄宗羲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诗,因好友多有殉难者而生发感慨,“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傀在灯前”二句,描述自身生存状态,是为自己没有“从忠杰传”的“惭傀”,亦是对遗民苟活于世的反思;与此同时,“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4]52句,却也道出了遗民生存不易。又如方以智《独往》诗,“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4]58句亦是此类情感表述的典范。遗民诗人追求自身道德理想的完善,看重节义胜过生死,因而不惧死亡;但每每痛哭旧友,则是哀叹同道者的零落与自身行道的孤独。
(二)出处行藏
明清易代之时,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成为主流,士人普遍希冀有所作为,或身体力行光复华夏之举,或尽己之力为传承文化做准备。满清统治巩固后,士人事功已不可为,转而依靠“立言”谋求不朽,参与修撰《明史》来实现遗民的自我价值,这也构成了清政府与汉族士人“合作双赢”的局面。但黄宗羲遣子百家入馆修史,自己始终游离其外;万斯同是修撰《明史》的主笔,却终身不领清朝俸禄。黄、万诸人以气节彪炳千秋,其谨慎的态度尚可视为不违本心;但就其他遗民而言,世俗眼光不免让人顾忌,甚而变成道德绑架,“况且宗国已淪亡,他们因守节而受到的煎熬困苦,不到死亡,没有底止。”[11]此外,归隐者对其“遗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价值认定,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仕进之路不可行,保持自身尊严和独立人格是遗民诗人最大的追求和坚守。不食周粟在此时并非指完全不与新朝合作,“遗民与非遗民的界限,仅仅在于作为旧朝之‘遗,能不能坚持不跟作为政治实体的新朝政权发生直接君臣关系。”[12]而以文化认同为理由不仕新朝者,才能始终保持初心。“清初舆论在议事论人的时候,事功和社会实效等考虑,往往要较道德空言来得更为重要。黄宗羲对易代期间,汉人在纾解民困前提下与新政权合作的认可,正可以用来说明此点。”[13]因此,周亮工仕清后的作为在当时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吴伟业自陈“误尽平生是一官,”[7]176也说明了他的出仕有“用事”目的。
(三)人伦范式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伦理规范、道德信仰与个人情感之间的矛盾格外突出,表现为私情与公理的尖锐对立。忠孝之间,“更有深层意义上的精神和肉体、家族和个人、生存和死亡的对立。”[14]明亡之际,不少人以“尽孝”之名出仕新朝,如吴伟业被家人劝阻自尽,后又迫于母命入仕,后半生失节之恨凄凉之情每每溢于言表,其诗感慨“我因亲在何敢死”[8]260,虽有推卸失节责任的成分在,也的确折射出忠孝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有人在两难中选择了“忠”,如郑成功拒绝父亲郑芝龙的降清要求,坚持“移孝作忠”,愤言“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父教子以贰”,认为“忠”的伦理价值显然更高。
人伦并不只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发乎本心的情感激荡,如明末才女商景兰在丈夫祁彪佳殉国之后,为抚养子女而苟且偷生,感叹“公自垂千古,吾独恋一生”,“自”与“独”明确地表达了她对丈夫选择的认可,亦透露自己对未能殉国殉夫殉情的遗憾。“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句,暗示子女还要抚养,不死的选择并非错误;相较于死,活着更切合人心符合人情。何况“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4]25,即使生死殊途,两人俱都无愧名节,“贞白”之心互相成全。商景兰享寿既永,一生饱经风霜,却也始终保留了几分遗民情结。
(四)时代困局
有清一代,汉族士人的生存空间都远小于之前历朝历代,文网的严密,异族异质文化的冲突,追求精神不朽的无望,都是士人沉重的心灵枷锁。清兵入关之初民族矛盾尖锐,汉族士人的仕进之路颇受阻碍,“科场”、“奏销”诸案更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身心戕害。之后,康熙优待汉人士大夫,优容明遗民,但对文人的控制未曾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也渐严密;康熙试图“以君道而兼师道”,文人“帝王师”的政治理想已无实现可能。武装反抗斗争在清初尚有较多,至康熙二十年前后,天下承平,文化界也渐从消极抵抗转向积极合作。时移世易,遗民情绪逐渐消解,遗民身份的坚守日益艰难。
“贰臣”周亮工出仕清朝,亦是受明末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使他确实在新朝平定天下、安抚百姓中颇有出力,却屡遭诬陷,锒铛入狱,险些丧命。这种结局使他怀疑当初的选择,诗句“出处抚微躬,难将铁铸错,生死空踌躇,悢悢两齿腭”[15]129-130,“出处吾全误”[15]317,抱怨“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15]513-514。现实残酷让人难以接受,他“强烈表达出自己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不满情绪,这在清初贰臣中很具有代表性。”
清朝统治渐趋稳定,抗清斗争渐归沉寂,遗民亦知反复之事不可为;何况康熙文化政策屡出,三藩之乱尚未平定即开“博学鸿儒科”笼络人心,又谕开《明史》馆编修明史。不管是被其“崇儒重道”的姿态所迷惑,抑或是对“以史传心”、承继道统有所期待,遗民士人对清政府的抵抗态度逐渐转变。冯班《朝歌旅舍》一诗颇有意味:“乞索生涯寄食身,舟前波浪马前尘。无成头白休频叹,似我白头能几人?”[4]19各种原因导致多数诗人逐渐退出遗民群体,“频叹”暗示冯班曾多次亲见同道者晚节不保,他著一“休”字风格自显;而末句“似我白头能几人”,既有自矜名节的骄傲,亦暗含同道者渐少的悲哀。就顾炎武诗集观之,与其经常酬唱的“李处士因笃”、“朱处士彝尊”等,本是海内大布衣,后却均应“博学鸿儒科”,离开遗民群体。
顾炎武关注史学研究,从政治遗民转为文化遗民,被举荐“博学鸿儒”科时说:“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
他看淡世事沧桑,深知恢复无望,但坚守“遗民”身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影响世风舆论的导向。黄宗羲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诗句“好友多从忠杰传,人情不尽绝交篇”[4]52也是感慨深沉。面对这种局面,那些真正重视气节的遗民只能无奈接受。康熙后期,天下承平日久,遗民已失去其生存土壤。士人保有遗民情结已实属不易,维持遗民身份则太过艰辛,很多遗民身在新朝的时间远比故明要长,始终在气节之上完美无瑕更是艰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选择和心态往往身不由己,而“遗民”也只能慢慢湮没于历史之中。
三、遗民诗人的文化根源
清初诗人,“凡遗民必是隐逸范畴”[3]57,同时往往也是著名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因而他们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艺术评价中,许多思想派别术语都会在不同场合使用,代表着不同的思维取向和审美倾向。因而,遗民诗人作为中国“隐逸文学”的典型代表之一,其诗歌也有典型的隐逸美学倾向。
遗民诗人的作品中,最突出、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当是道家,尤其是庄子哲学。而在儒家和佛教思想的渗透下,它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文艺精神的思考中,突出强调了道家庄学(以及受庄学影响的玄学)作为文人之思想根源,乃至直称庄子哲学为“逸的哲学”。从“逸”的思想方面来看,“庄子自己说他‘以天下为沉浊;而他的精神是‘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这是由沉浊超升上去的超逸,高逸的精神境界。
所以他的《逍遥游》,《齐物论》,都可以说是把‘逸民的生活形态,在观念上发展到了顶点。因此,他的哲学,也可以说是‘逸的哲学。以他的哲学为根源的魏晋玄学,大家都是‘嗤笑询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的,这可以说都是在追求逸的人生。”[17]遗民诗人的思想根源也包含释家或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精神因素。“在诸佛教流派中以禅宗的美学思想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禅与‘逸之关系较为间接,主要表现为‘禅境这种心性领域,通过影响‘意境这个审美领域,然后再对‘逸境这个审美层次施加影响。禅境对意境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盎然静趣的追求……‘禅境与‘逸境,除了皆尚‘空灵,二者皆以简为尚。禅是讲‘空无的,禅的哲学境界和审美境界都是以‘空为其显着特征的。‘
逸也是如此,有了‘空方能有审美主体的精神上的飞跃,方能达一种物我两忘、心物交融的审美境界”;“禅宗特别尚简,以至简到不能再简。慧能讲‘顿悟成佛、‘无念为宗理论,其最大特点就是一‘简字。无须打坐念佛,只要心中有佛,既可‘顿悟成佛,抛弃了那种烦琐的经院佛学,提倡一种简易直捷的功夫。‘逸也与此相通。禅宗本来就与道家有某些共通之处,因此,‘逸的审美观念与禅宗哲学、审美意识相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18]总之,佛教、禅宗追求自然、宁静、空灵、简约的思想精神,对逸品绘画也产生重要影响。
逸品在儒家那里也可以找到思想根源。儒家虽然注重入世,但也不排斥隐逸、出世、独善其身,相反,隐逸、出世、独善其身其实是儒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语》记载有许多相关的孔子言论,《论语·微子》篇还明确出现“逸民”一词:“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9]梳理历史可见,清初遗民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批遗民,他们自然也会从历史上的遗民、逸民那里吸取精神养分。整体而言,遗民文学家对政治、社會的黑暗混乱所作的消极而彻底的由人生价值、人格尊严所发出的反抗,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形成另一有重大意义的生活形态。
孔子首先提出此一生活形态的价值后,由《史记·伯夷列传》到《后汉书·逸民传》的成立,对于守着这种生活态度的人们,给予了我国历史上应得的确定地位。“绘画由人物转向山水、自然,本是由隐逸之士的隐逸情怀所创造出来的;因此,逸格可以说是山水画自身所应有的性格得到完成的表现。而其最基本的条件,则在于画家本身生活形态的逸。”可见,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对于隐逸文化的形成,对于隐逸艺术家创造逸品艺术作品,尤其对于清初遗民诗人,也有着重要的文化影响。
分析可知,儒、释、道三家都具有那种从内在的人性欲望到外在的文明社会的种种束缚和诱惑中的逸出、反思的精神。道家、释家主张出世、忘世,这种逸出的精神,这种减的功夫和力量,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如道家主张的虚静、心斋、坐忘,以及佛教禅宗所讲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20]。以积极进取为主要体现的儒家同样也具有一种逸出的精神。孔子也并不排斥隐逸、遁世、独善其身。孟子就说过:“养心莫善乎寡欲”(《孟子·尽心下》)。这在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对于清初遗民诗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明清易祚,异质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使士人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动荡多变的外部环境必然会对诗人之心产生极大影响,他们的文学实践,也让这一时期“志之所之”的诗歌发出了诗人的心声,一扫有明以来的颓势而重新焕发光彩。清初诗作风格或昂扬或低回,都是对诗歌言志抒情传统的回归、继承和发扬。由悲愤激越到冲和淡远,前后期诗风迥异是清初诗人的普遍特点,除了自身心态的变化,王渔洋执文坛牛耳后提倡“神韵”诗风也有重要影响。
但在对明清之际诗人的评价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语境仍有很大影响,对鼎革之际君死臣殉的伦理标准有所苛求,而忘却了历史中个人艰难求生时内心承受的痛苦,忽视了其中人性的代价。“在这个道德最大化的要求中,个人的正气、意气和性格锋芒,被用作权衡一切行为的标尺,全然不顾个体生命的价值。”[21]清初诗人的遗民情结与生存困境之间有着太多的勾连,社会变换中的士心、诗心的内在张力值得更多关注。而诗人们波澜壮阔的人生之路与百转千回的个人情感,可以给生于其后的文人带来更多心灵上的震撼和反思。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的遗民诗人,通过诗歌来感慨身世,怀念故国。其诗学主题包含生死两难,出处行藏,人伦范式,时代困局等诸多内容。从文化根源的层面来看,遗民诗歌具有典型的隐逸美学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1]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7.
[2] 顾炎武.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M]. 吴宓,评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85.
[3] 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 夏琳.闽海紀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49.
[6] 周劭.清诗的春夏[M].北京:中华书局,2004:9.
[7]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 钱仲联.明遗民录汇辑?序[J].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16.
不同文学书写中的中华琴文化 陈洪;4-9
还原一个本真的孙犁 张学正;10-15
创作现场与传播流变——《骆驼祥子》文本变异初探 刘运峰;董仕衍;16-25
精英的离散与困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绅缙世界 罗维斯;26-36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