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3-06-1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308次
摘 要: 文章借鉴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界“惯例”概念,反思了我们一般习以惯之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作为一种特殊的惯例,艺术观念的确立不是艺术家或批评家个人的成果,而是艺术界各行动者彼此协商而又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艺术观念一旦确立,它又会加入到艺术界的文化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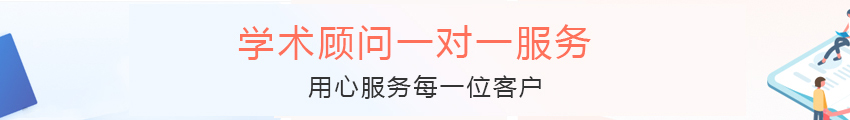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论文摘要】文章借鉴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界“惯例”概念,反思了我们一般习以惯之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作为一种特殊的惯例,艺术观念的确立不是艺术家或批评家个人的成果,而是艺术界各行动者彼此协商而又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艺术观念一旦确立,它又会加入到艺术界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惯例机制起着规范和筛选的作用。对于“存在着艺术与非艺术之分”等这类传统艺术观念而言,其作用甚至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实现的。
【论文关键词】艺术观念 艺术惯例 艺术体制
我们一般习惯于通过某个名字来判断作品的归属,并将之视为作品的唯一创造者,譬如书页上的作者姓名、国画上的印鉴、雕像底座上的签名,或是某本着作中出现的诸如“罗伯特·史密森的名作《螺旋形防波堤》”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习惯于把意味深长、匠思独运等褒奖之辞赋予某些作品,这其中既包括了达芬奇着名的《蒙娜丽莎》,也无疑应该包含杜尚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显然,支持着上述看法出现并存在下去的不只是那些艺术品本身,也需要某些特定的艺术观念,即丹托称之为艺术理论氛围或艺术史知识等之类的东西。在此层面上,艺术观念在艺术界中的重要地位便相当引人深思。我们或许会希望解答一个问题,艺术观念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如果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结果可能会令我们瞠目结舌:所谓艺术观念可以说是艺术界惯例机制的一个构成成分,而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我们习以惯之的艺术观念,我们或许可以为美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所谓“惯例”,从宽泛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而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艺术观念一直被视为艺术界惯例的一个重要成份。霍华德·贝克把艺术界理解为一个艺术界公众通过协商而进行合作的关系网络,而在各种关系中起着协调和规范作用的便是艺术惯例。它包括了我们每个社会化的公众都普遍认同的艺术观念,譬如诗歌与小说这种体裁上的划分,或什么是艺术的判断标准,等等。正是对这些艺术观念的认识划定了一个艺术界的外部边界。它也包括了更加专业化的美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即对艺术史、艺术风格、艺术价值、艺术史中的重大问题等各种划分及评判标准的了解。因而,虽然将艺术观念冠之以“惯例”之名似有不敬,但是,恰恰只有这么做时,上述那一系列的艺术现象才似乎变得合理。设想之下,如果杜尚那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放在了达芬奇时代,它便不可能获得此殊荣。
就此而言,从惯例的角度看,我们对任何艺术观念本身的思考便都需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艺术观念上的反思:所谓的“美”、“崇高”、“艺术性”等术语的有效性成为了问题;我们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风格的区分无法离开对那一阶段艺术史知识的了解;甚至于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美学论文或艺术评论也涉及了既定的规范。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艺术观念的开放性,因为视艺术观念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界惯例,这便赋予了其动态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所谓的永恒不朽的艺术价值便可堪质疑。实际上,近一百年的艺术发展已经极大地冲击了最基础的艺术观念,当各种拼贴的碎布、毛发用于绘画,当各种现成物被作为雕塑而展示时,我们从小就被教授的艺术门类的区分业已不再有效。
在上述语境之下,一个似乎顺理成章的问题便是,如果把艺术观念视为一种惯例,而且是一种随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而转换的惯例,那么这些艺术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发生作用的?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恰已涉及艺术观念问题最为核心的东西。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无疑将成为我们当下反思艺术及美学理论的基础。
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便是艺术观念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是某些具有特别才能的个人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品与艺术观念,但是从一个艺术观念出现并最终得以确立的过程来看,它并不只是某位艺术家、批评家或美学家个人的一时一地的宣言及阐述。一种思想或一种风格只有被艺术界公众广泛接受,成为一种共识时,才能真正成就其“艺术观念”的独特地位,艺术观念在艺术界中的最终位置总是无法避开那些外在言说者的那诸多因素。用霍华德·贝克的话来说,艺术观念便是艺术界中的公众在合作生产的过程中,彼此协商与相互妥协的产物。有关这一点,我国先锋派艺术的崛起便颇可玩味,随着1993年方力钧等艺术家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大获成功,我国艺术界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势,并获得了中国艺术市场与评论界的广泛认可。可见,只有在经历了无数的冲突、角力、说服与协调之后,先锋艺术观才得以在中国扎根。因而,艺术观念不是艺术界先在的规范性力量,而是在艺术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发展的。作为各主体之间达成的一致决定,特定的艺术观念只在特定时空中合法而有效,它只是那一特定语境中群体的一致认同。
随着艺术观念的确定,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艺术观念在艺术界再生产机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按照艺术社会学的思路,把创作、评论、欣赏等艺术实践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进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对艺术观念的种种探讨置于艺术界各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思索它是如何产生、又是以何种途径进入再生产的过程的。
艺术观念的产生固然是艺术界公众协作下的产物,但是一旦新的艺术观念成为惯例之后,它也会成为维系这一体系强有力的支持力量。也就是说,艺术观念会作为艺术界的惯例机制控制或影响着艺术实践的进程。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事实便是,大量的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都是从大学、书店、博物馆等这些专业的艺术机构中习得了有关的知识。具体来说,艺术观念具体两种特殊的功能。
第一,艺术观念作为惯例机制的一个特征是它的筛选功能。正因这一特征,它与艺术机构之间联系远比我们所见的更为密切。正是在艺术机构之中,艺术观念作为一种规范性惯例运作着。艺术机构在艺术界中充当了彼得森(RichardA.Pete~on)等文化社会学者讨论甚多的把关人(g~ekeeper)的作用。所谓“把关人”,即在艺术界的生产一消费环节中,根据既定惯例的相关规则,发挥过滤功能的各种艺术机构。从这个角度来讲,艺术机构就是一种筛选系统。亚历山大(VictoiraD.Alexander)以印刷系统为例,列数了在其中担任把关人的各环节。作者写出作品,直至读者读到该作品,其间包括了出版商的审查、批评家选择什么书加以评论以及书店决定把什么书放上书架的各项环节。换而言之,一部作品在分配过程中必须经历一系列筛选机制,才能到达读者手中,而在此过程中,大部分的作品都被过滤在外。当然,大学、各种奖励系统、官方艺术评判机构等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在一个艺术界中起着整合协调作用的艺术观念,是通过筛选与划界来实现其整合与协调功能的。为了合作的顺利展开,它总是要将那些不符合惯例的艺术实践排斥在外。
第二,艺术观念之所以能发挥上述的筛选功能,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惯例,构成了艺术界特有的倾向性结构。从某种角度上说,惯例就是结构本身。在贝克对惯例的描述中,他的一个判断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在协作过程中,惯例总是可以让一项合作效率提高、简单易行。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经验获得这一判断,但其背后却蕴含了深深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问的张力关系。换而言之,艺术观念在艺术界中是以内化的结构的形式发挥作用的。
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者之问不是彼此对立,而是互相作用的动态关系。正是结构与行动者的行动之间的递推性互动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当吉登斯讨论结构二重性原理时,他指出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结构总是内在于人的行为之中。“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吉登斯有关“结构”这一发现,实际上已经被许多社会学家所关注。譬如费什在讨论实践与规则之间关系的问题时,亦批驳了那种较为僵化的结构论,而倾向于与结构二重性相近的立场。费什相信,规则必须先于实践而存在,否则实践将会是无原则的,但是“实践早已是原则性的,因为实践每时每刻都由一种(法律、篮球)实践是什么的理解所定制,这种理解总是能被表述为规则的形式——那规则对于局外人而言会是晦涩的——但它却不是由规则所产生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规则或结构总是持续地内化于个人实践之中,而实践本身就在规则中结构化。
在结构二重性的理论框架之上,吉登斯向我们清楚地勾勒了惯例如何成为了一种结构性规则,这是通过循环往复的重复过程而养成的一种信任机制:
惯例……是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日常”这个词所涵括的,恰恰是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时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各种活动日复一日地以相同方式进行,它所体现出的单调重复的特点,正是我所说的社会生活循环往复的特征的实质根基……社会生活日常活动中的某些心理机制维持着某种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感觉,而这些机制的关键正是例行化。
吉登斯这里所讨论的“惯例”强调的是其例行公事、重复操演、乃至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的那一面,他主张个体行动者对某种连续性的信任感是“惯例”得以结构化的根源,而这正是所谓“艺术惯例”的一个关键成分,它尤其存在于以常规惯例形式存在着的那些艺术观念之中。正是这一性质保证了那些基础性的艺术观念得以持续下去:譬如艺术与非艺术能够区分,并应该加以区分;或是艺术有高雅、通俗之别等等。我们可以毫不惊诧地发现,这些观念总是以某种简化或不假思索的方式实现的。所谓艺术惯例不仅作用于意识领域,也深入到无意识之中,这一特征不仅是使艺术惯例成为艺术界一个有效的整合性力量,也是它最终能促成艺术观念被结构化与体制化的一个核心要素。对此,费什的一番陈述或许显得更为尖锐并富于警示性:惯例“不会带有丝毫的反思性……他不是自由地去选择或创造他自己的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系列的意义已经选择了他,并且在理解、阐释、判断等行为中,甚至在他所正在做着的行为中,这些意义已经制定出了其自身。”
第三,尽管我们已经讨论了艺术观念所扮演的结构性功能,但这里,我们仍需要意识到结构另一方面的特征:各种艺术观念在艺术界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实际上并不如上文所表现的那样僵化。或许我们在布尔迪厄那里,可以获得有关艺术界中这一特殊结构的另一角度的理解。
作为布尔迪厄对场域结构的关键概念之一,“惯习”发挥着与“惯例”相近似的整合功能,并在场域结构化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在他那里,“惯习”系统是一种行为倾向系统,也就是说,结构产生惯习,并通过惯习控制了实践。但这种控制不是机械而凝固的,作为一种性情系统,惯习借助倾向性来引导并限制实践,这此过程中,倾向性结构允许了与“保存冲动”相对的“创造冲动”的存在。
惯习包含了我们所继承的看法,但它并没有建构一种制约我们必须如何行为的促进因素。……我们并非机械地或自动地实现任何安排,我们可以说是先于其规定,固有地拥有了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艺术界行动者的行为既包括有意识的行动,亦含有那些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解释的那部分行动。惯例固然是围绕着一种新出现的艺术观点,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的纯熟而形成,但一旦它被结构化,这种体制化的艺术观念就能颇有效率地把个体认同与组织机构的支持及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独立于作品却影响艺术生产至深的一种规则。结合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加以理解,所谓艺术界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其实也充分地允许了创造与突破的重要地位,而这也正是艺术界及其艺术观念能够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不管如何,从艺术观念与结构的密切关系来考虑,我们传统美学思想所经历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例行化”或是“倾向性”的思维特质密切相关。譬如维特根斯坦语言学转向中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罗兰·巴特对“作者”地位的质疑,等等,这些思想的出现都是对传统美学中“例行化”思维模式的一种反对。
所谓的艺术观念都经历了它在艺术界中社会一历史地生成、它的逐步体制化、及其作用于艺术再生产的过程。如果从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艺术观念,那我们或可实现一种认识上的转化,即从关注艺术观念的内容转向它在艺术界中的特定功能。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对于批评家、美学家和艺术家所起的作用或许也会有别样的理解。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所承担的那一部分职能,正是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创造与扞卫艺术观念的那一能力。当然,用艺术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创造”这个词颇有点将其社会职能神秘化的危险,因此,本文可以采用鲍曼的“立法者”来指称这群人的社会角色:在艺术界的艺术活动中,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承担着使一件作品的艺术资格合法化,以及赋予艺术品在社会历史中的神圣地位(即艺术价值)等职能。简而言之,也就是为艺术立法的功能。美学家和批评家的行为“包括了创造以及维持基本原理,依据这种原理,所有其他的行为变得具有意义而有了实施的价值”。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们所进行的这种艺术实践,是艺术界的合作生产的核心,正是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体制化,及其参与到艺术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的艺术实践得以沿着我们能够理解的轨迹而进行。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