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9-06-1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205次
摘 要: 摘要:在人类学发展的同时,研究者对仪式的研究也从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延伸到了学术之外。仪式的重复性、表演性、群体性等基本特征,使对其的辨识在得到强化的同时,也成为仪式内涵发展和深化的桎梏。仪式感是从仪式中衍生的情感变化,对仪式感的过分看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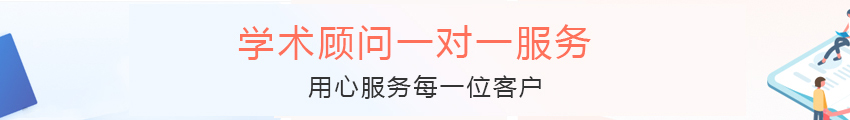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在人类学发展的同时,研究者对仪式的研究也从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延伸到了学术之外。仪式的重复性、表演性、群体性等基本特征,使对其的辨识在得到强化的同时,也成为仪式内涵发展和深化的桎梏。仪式感是从仪式中衍生的情感变化,对仪式感的过分看重会消解思维深度。对仪式行为以及仪式行为研究的反思,有利于辩证地对待仪式本身的发展,而正视仪式因程式化所导致的思维固化,更有利于在扬弃中强化研究成果。
关键词:仪式;仪式感;仪式内涵;思维深度

在人类学视域下,仪式被认为是一种人类的群体社会行为。伴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创立及发展,仪式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以及一套具有特定观察和研究对象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仪式学。仪式从人类早期纯粹的“宗教实践活动”,到现在成为涵盖“社会实践活动”甚至日常生活行为的过程,已历经百余年。在这百余年中,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英国仪式学家特纳、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为代表的大批学者,为仪式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人类从不自觉、感性地组织、参与仪式,到自觉、理性地利用仪式。从宗教到社会、由神圣至凡俗,仪式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仪式也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当仪式无处不在,甚至被人类刻意追求时,仪式中的负面因素也随之显现。首先,在被人类过分提倡时,仪式中的形式主义会随之产生,如有些社会交往仪式的形式大于内容,人际关系与情感交流让位于仪式程序,使仪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其次,当仪式的严肃性被不恰当地夸大时,将导致人类对它产生类似“迷信”般的依赖,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用仪式去证明做事的态度。其结果导致在没有仪式或仪式不够隆重时,事情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如在婚礼仪式与成人礼仪式中,当仪式的严肃性被过于强调时,婚姻与成长本身应具备的内容便会被淡化,使仪式参与者很容易沉浸在仪式中不能自拔。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仪式在一般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的程式,这使得仪式存在循环与重复的特性。在此之外,仪式还不允许随意改变,它的过程几乎都是固定的,这样一来,当仪式被人类过分依赖时,人的想象与思考能力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涂尔干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就提到,“如果有人问一个土著为什么要举行仪式,他会回答,他的祖先总是如此奉行,他应该遵照他们的榜样……他觉得他在服从一道律令,履行一项义务”[1]264。从中可以看出,当仪式成为一种惯例之时,人类与之相关的思考也会因此而懈怠。
一、仪式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实践形式而言,仪式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即使是作为巫术而存在的早期仪式,它也蕴含着人类渴求探索自然的火种。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观点:“当我们更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巫术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么,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2]
87经过漫长的巫术时期,仪式取得了本质层面的进步,它从一系列形式中生发出了人类本性情感,这促进了早期宗教的形成,其内涵主要表现为爱与救赎、恶与禁忌。进一步来讲,宗教活动通过仪式为大众展现出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异的世界。仪式的主持者在仪式过程中对仪式的参与者宣扬:人类世界属于所有世界中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出生之前以及死亡之后都应该得到安宁,实现这种境况只能通过信奉宗教的途径,而信奉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参与各种仪式。
如在原始宗教中,原始人主要从万物有灵及自然崇拜中获得精神上的寄托,并实现物质层面的目的与利益。这种原始宗教更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更而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需要的结果。一些民族甚至认为宇宙的形成也起源于仪式的发生,如雅利安人相信世界是在献祭仪式中被创造的,“起初遵照神圣秩序工作的神灵经由七个步骤创造了世界……但起先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直到神灵进行了三次献祭……世界从此变得生机勃勃。
太阳开始在空中运行,确立了季节的更替,三个供献祭的牺牲者产生出了各自的后代”[3]8。到了人类真正以宗教参与自身生活的时期,宗教的教义、体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其仪式表现也逐渐形成了固定、重复的模式。可以看到的是,世界各地宗教的创立契机各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与主旨也存在相似之处。如佛教中的法会,以对亡者进行助念的仪式,使教徒凭借“咒语”与人类之外的虚空法界进行沟通;天主教以洗礼、忏悔、坚振、圣体、病人傅油、圣秩、婚姻7件圣事,从而达到人与天主的沟通,天主教徒从这些仪式中感受到天主的力量;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通过教义严格管理教徒,并让教徒在各种朝圣行为中靠近真主。
仪式成为宗教活动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关系着人类的心灵世界,而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内容必须通过行为表达,仪式正是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它把集体的心凝聚在一起,其功能就是创造、保持、再创造群体中的某些精神状态。由此看来,仪式就成为一种手段,控制者凭借这一手段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从而使社会群体在利益上、传统上、行动上达到新的统一”[4]86。
宗教在不断举行主题宗教仪式的过程中,强化了仪式的“重复性”,使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规范、程式的意义。事实上,行为的规范化在一定环境中是必要的,它体现的是秩序的掺入,仪式参与者在行为上的整齐划一不但能产生美的效应,而且能够形成凝聚性的力量。受弗雷泽的影响,诸多研究者认为人类的思想经历了由巫术至宗教,又由宗教至科学这样三个阶段。
然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巫术是人们在某种严格规定的仪式的基础上,力求达到特定结果的一种尝试。它的基础在于承认因果原则,即承认若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同样的结果就会随之发生。因此,巫术是原始科学。”宗教则来源于另外的路径,“宗教产生于不同的根源,在这里,有一种违背或不顾有规则序列以求达到结果的企图,在超自然的领域内起作用,具有摈弃因果关系的含义”[5]11。
也就是说,科学与巫术之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而宗教与这两者的关联则并不大,虽然罗素并未解释巫术与宗教到底从何而来,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源头,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巫术还是宗教,仪式都是它们行为组织的主要承载方式,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继承巫术探索精神的科学,也必然会存在仪式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从科学实践的表现来看,仪式行为含有对真理、事实的信仰态度,在探索过程中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并需要不断地重复。
与科学行为一样,仪式也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因此虽然科学仪式没有巫术仪式与宗教仪式那么显而易见,但就其行为表现的内在含义来看,科学实践同样包含仪式的特征与意义。尽管人类学学科从诞生到现在不过百余年的历史,针对仪式的专门研究更是短暂,然而人类仪式行为的历史却极其悠久。据李泽厚考证,当原始人在同伴的尸体旁撒上矿物粉时,这些具有特殊含义、原始物质化的行为便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起始,它的进一步发展即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6]4。
杨庆堃从另一个角度也指出,人类对仪式的需要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如葬礼、祭祀等仪式,它已经超出了原始宗教的范畴,也不是对未知世界的信仰,而是一种人类的生存策略,用以维系一个群体的完整,并用以对付亲密成员死亡后给他人带来的情感伤害[7]24。
这些对仪式源头的研究,几乎都属于宗教与科学之外的领域,偏近于人类的日常生活,拙文《人类学视野下的小说仪式书写》也总结出:“古代的‘仪式’大致分两种含义,一种作秩序用,将仪式作为行为规范,如韩愈《南海神庙碑》中有‘水陆之品,狼藉笾豆;荐裸兴俯,不中仪式’;另一种作法律用,用仪式指代法规与刑罚,《诗经·周颂·我将》中有‘仪式邢文王之典’。”[8]
由此可见,仪式在古代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严密的系统,在这种系统的支配和渗透下,文明在逐渐发展的同时,各种礼仪、仪式行为也变得越来越烦琐和复杂,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变得刻板、腐朽,成为冲突的导火线。在中国历史中,自明朝正德皇帝以降,西方传教士来华试图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时,中国大臣关注的重心不是如何实现发展,而是如何让这些“蛮夷”学会天朝礼仪,可以说,其时各种复杂的仪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文明保守、落后的标签。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在内忧外患中的一系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仪式思维与认知的改革。
二、仪式的内涵与特性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仪式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行为,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概念的重点在于突出仪式的群体性,简·艾伦·哈里森强调:“我们已经注意到仪式中的一个因素,那就是要由一定数量的人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感知同一种情感。独自消化一顿晚餐肯定不是仪式,如果一群人在同一种情感的影响下共同吃掉一餐饭,且时常这样做,那就可能变成一种仪式。”[9]16然而,群体性的行为很容易形成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从表面来看热闹非凡,实际内涵则可能无比空虚。
因为当群体性成为仪式的重要特性时,它就意味着拒绝孤独与摆脱孤独。在一场仪式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是人与物之间,建立联系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孤单可以导向深刻,李泽厚深刻地指出:“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才展示出了现代的内涵和人生意义。”[10]115不仅仅是鲁迅,几乎任何一位真正的智者都是孤独的,没有孤单,则无法深刻。因此,仪式的群体性是人类放弃深刻的一种行为模式,在仪式中,群体性的秩序是最重要的,这其中无须仪式参与者的思考,需要的是一致与附和,以及对仪式本身与仪式引导者的一种认同。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人性中无论是善的行为或是恶的行为,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得到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包括自我认同,亦包括他人对自我的认同。福山深刻地指出了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导致了文明的传播与战争的发生,不仅阶层与权力的产生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商品交换与劳动的行为同样需要认同,而在这些获取认同的方式中,仪式几乎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主持仪式的人便视为能与未知的世界沟通,这种能力使得仪式主持者在获取他人认同的同时,也获取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力。同样,在早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个人劳动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群体劳动才能有所收获,因此与劳动相关的仪式即成为群体的期待与寄托。其原因在于仪式的内涵与特性决定了仪式行为与人类思维有着高度的契合,无论是仪式的主持者抑或是仪式的参与者,都能从仪式中获取满足感。
在群体性之外,仪式行为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表演性与象征性,而象征性在一定意义上又需要凭借表演性予以实现,因此可以说表演性是仪式中最为根本的部分。但是,当表演成为一种行为的本质特征时,这种行为的深刻性就会受到明显地减损,行为本身的目的遭到弱化,受到重视的是仪式在表演过程中达到的效果,这样一来,仪式便有可能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如宗族祭祖仪式的实质本应该是培养后人“慎终追远”的品德,通过在仪式中对祖先的缅怀,对家族发展历史的诉说,达到教育后人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可变的是无法衡量的精神实质,不变的却是表演的形式部分。因此,在能量守恒定律的支配下,当精神实质减退时,表演形式就必然需要得到加强,仪式也随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杨庆堃在分析中国传统的哭灵仪式时指出,一些刚过门的新娘对新家庭的死亡成员缺乏感情,特别是当死者是与新娘发生过不愉快的婆婆时,新娘的哭灵便完全是一种表演,而表演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仪式而导致的家庭不和与疏远便成为一种必然,仪式参与者又很少会反思家庭矛盾中的情感根源,而是将问题与仪式表现相联系,使仪式在表演的路上愈行愈远。重复性是仪式的另一重要内涵,因为仪式需要被后人继承,也需要巩固,对于发生频率极低的行为,即使它的内涵再丰富、场面再壮大,也早已湮没在历史当中,这种行为无法称为仪式,只能说是一种偶发的行为现象。
反之,当一种行为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其内涵不断扩大时,这种行为自然便成了仪式。荣格对于仪式的重复性特质十分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将重复视为仪式不可或缺的成分,不如说那仅仅是一种人类的本能使然,“本能行为的最大特征就是它具有普遍一致性和可重复发生性”,“本能起源于反复重演的意志行为,这些意志行为先是个别的,以后则成为共同的”[11]4。
甚至可以说,在有些仪式中可能含有的重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也会逐渐消减,只要行为被一遍遍地重复,它的仪式外壳也始终能被保留下来。进一步讲,当人需要利用仪式来达到一些目的时,哪怕这种仪式行为不具备任何内涵意义,只要它能被固定重复若干次,也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习惯进一步演变为传统,传统继而变为仪式。
如在中国西北地区,男人在聚餐过程中一般都有划拳的习惯,这种习惯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缺少言语交流的环境,于是以这种行为作为替代,但当他们每次外出吃饭都要划拳时,划拳便会固定为一种在吃饭过程中需要进行的仪式,如果某次因故不能划拳时,在座的人则需要对他们这种惯性仪式的暂时中断做出解释,并做出相应的承诺,否则就会引起其他人的猜测而导致关系的疏离。
由此看来,仪式存在的意义在于仪式主持者或仪式控制者对它的期待,即通过仪式达到掌控他人、确立权威、获得利益、统一认识、传播教化等目的。在仪式行为过程中,刻意营造的环境氛围也会加强这种效果,因此仪式在一些场合中容易超越它本来应该有的界限———凝聚仪式参与者的情感、建立一种群体的秩序等,或者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甚至难以控制参与者的情绪而成为暴乱行为的根源。
三、对现阶段仪式泛化的反思
当人类过多地赋予一种行为美好的意义时,这种行为便会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标签的范式,甚至成为衡量其他行为恰当与否的标准,当下社会中不绝于耳的“仪式感”正是如此。从媒体对仪式一词的反复利用,到大众试图淡化仪式的群体性并使其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时,仪式已经有了泛化的趋势,当仪式这种行为被模糊为仪式化、仪式感时,仪式本来的含义便遭到了进一步的曲解。事实上,仪式的泛化趋势早已遭到了质疑和反对。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提到:“仪式分析经常受到的一个批评是,它过于普遍化。仪式无所不在,但如果一切事情都是仪式,那么什么不是仪式呢?”[12]35
这种观点体现出的是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锋。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仪式研究者来说,仪式的发展显然越盛大越好,这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而且可以随着这种行为现象的频繁出现彰显这类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德国学者洛蕾利斯·辛格霍夫在《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中不断强调仪式对于人类情绪的安抚作用,她甚至认为唯有仪式才能使人渡过最艰难的阶段,如葬礼能缓解家人的痛苦,成人礼可以让青少年安全、顺利地过渡到成年阶段,怀孕、生病等特殊时期的不安也应该通过仪式得以解决,甚至在社会危机来临时,也只有仪式才能成为人依靠的对象,“借助仪式,人们能够克服社会存在的差异,建构社会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仪式使人们有可能在共同的行动中邂逅、相知并相互融合。仪式传递情感上的安全感和社会可靠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13]5。
辛格霍夫的观点无疑将仪式推向了一种极端,照她看来,仪式可能重新回归为一种巫术,或行为上的“毒品”,要不然,何以在人生无论喜悲、病痛或灾难的时候,都有仪式的身影呢?仪式是否真的拥有能够扭转人类情绪的强大力量?这个问题可先放置不谈,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人民为主的民众,对生活的仪式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却是不争的事实。阿克瑟尔·米歇尔斯从生物行为的角度指出仪式行为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人类仪式活动和动物行为相似,动物总是循环式地重复某些动作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人类的某些活动也是由基因所决定或是从进化中形成”[14]35。
在这里便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的生产活动必须存在意义,换言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价值。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语言或是行为,意义越重大,其价值也越高。可见,在行为的内涵中注入意义,不仅有利于行为本身价值的提升,而且能延伸出更多的价值存在。而利用仪式来彰显意义,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然而,仪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加重”的符号,以致使日常行为与仪式不断地结合后,日常行为完全偏离了其原本的意义,无法到达仪式行为的层级,而成为一种只具有仪式外壳而无实质内容的方式。
具体来说,由于仪式的历史性、神圣性、严肃性在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呈现,使得许多人把仪式等同于生活美学,并与认真、不苟且、精致、情调等同义。为了使这种认知更加普遍化和更容易达到迅速传播的目的,许多人更以“仪式感”取代“仪式”,进而将仪式感指向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试图以仪式转换认知,传递内心深处的虔诚与信仰。
一些关于“仪式感”的书籍,如《生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给潦草的生活一个巴掌》《仪式感:把将就的日子过成讲究的生活》等,为仪式在日常中的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一日三餐需要仪式感,喝茶吃点心需要仪式感,朋友之间礼尚往来需要仪式感,甚至工作、穿衣戴帽、休闲旅行都以“仪式”为名时,仪式的泛化可能已经成了“日用而不知”。
事实上,这种对仪式感的理解早已脱离了仪式本身的含义,仪式感的滥用使仪式中的象征意义与表演意义遭到了曲解,而且刻意将一种现代意义的价值观与古老的仪式相结合,力求为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找到依据。在现代西方科技的冲击下,“拜物教”成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而与其说这是一种信仰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鲍德里亚以西方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为背景,提出信仰从精神到物质的转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观点暗示了在传统宗教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指导有缺失时,仪式感便成了一种替代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宗教来看,“拜物教”中的仪式感指向没有具体的概念及规范。
因此,所谓的仪式感仅仅是为了遮盖“拜物”层面上赤裸裸的欲望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仪式感将群体仪式降为个人仪式时,表面上是对人的思维解放,实际上则是对人精神信仰的巨大冲击。仪式感只能从注意力的转换方面带给人以安慰,却无法解决人在精神层面上出现的实际问题。
一些仪式性的行为转而成为现代人所关注的对象,他们不需要具体的信仰对象,却需要一种方式来舒缓情感方面的压力,因此极富象征性的仪式显然可以回应这样的期待。然而,这种没有具体指向的仪式行为显然是虚弱的,因其背后缺少真正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只是通过人对一种日常行为的不断重复,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仪式,在这样的理解下,“仪式感”只能流入人云亦云的地步。进一步来讲,这种所谓的“仪式”会转化为一种形式主义,这是因为人在精神健康时,勤奋、创造、专注等能力显然属于应该具备的素质,而非通过一种形式化的行为进行刻意地附加或追求。
换言之,仅仅依靠改变生活方式无法构建仪式的意义指向,更加不能产生仪式的象征力量。仪式感被泛化后的无意义还表现在思维的固化上,因为仪式行为是习得的过程,需要通过传承而掌握,因此后代人在进行仪式时,无须思考每一种行为的含义,更无须思考为何要以如此的行为来表达,只需要按照前人的已有方式去进行即可,这样一来,原本需要体现思考价值的行为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模仿。
比如当有足够多的人号召使用钢笔来替代中性笔,或是吃饭都必须铺桌布等行为来体现仪式感时,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不经过思维的过滤,直接变成一种固定的意识,最后形成一种仪式的教条主义,而仪式本身的含义则遭到了刻意的误读与漠视。当这种机械的仪式在失去了严肃性、秩序性等内在含义时,仪式行为便会反向地影响思维,进而趋向于浮躁与虚无。
四、结语
对仪式意义的审思并非在近代才有,先秦墨子反对儒家的丧葬与祭祀即是对仪式行为的一种否定。应该说,仪式行为只是一种思维方式传播的结果,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过度地强调规范、权威等特性时,行为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含义,成了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仪式与形式几乎同出而异名,当仪式变为形式时,它便成了规范的机械行为。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在母亲洗盘子的厨房里,小女孩明白了,多年以来,每个下午,在同一时刻,这双手要浸到油腻的水里,用粗抹布擦瓷器。直到死,她们都要屈从这些仪式。吃饭、睡觉、打扫……岁月不再向天国攀登,它们在一张平展展的桌布上摊开,千篇一律,色调灰暗;每一天模仿前面一天;这是无用的、毫无希望的、永恒的现在。”[15]
243事实上,人的存在需要延续一种关于意义的思考,仪式或许在最初的时候承担了意义,但当其呈现出一种泛化的趋势时,意义显然会消失在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当中。畸形的仪式感正是对仪式行为泛化的鼓吹,这种结果并不能使仪式具有意义,只会使其走向僵化,故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许多仪式行为都需要受到反思和质疑。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似积极的思维同样会导致消极的行为,厘清思维的理性与盲目,引导行为方式的科学,这是仪式反思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J.G.弗雷泽.金枝[M].张泽石,汪培基,徐育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M].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4]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M].瞿铁鹏,殷晓蓉,王鉴平,俞吾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历史刊物推荐:《史学集刊》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双月刊)创刊于1956年,是全国历史类核心期刊。创刊近半个世纪以来,本刊一直秉承“传播学术薪火,弘扬历史文化”的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学术精品,提携了大批优秀学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