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0-12-10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163次
摘 要: 美国摄影师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在1889年曾拍过一张名为Suns Rays的照片黄昏被百叶窗切割,均匀、细长的光影伸出古老的手臂,悄然笼进房间; 一位母亲正在写信,她的眼神低垂、专注,不受外物侵犯,黄昏的光影打在她平静无波的脸上,似乎把时间也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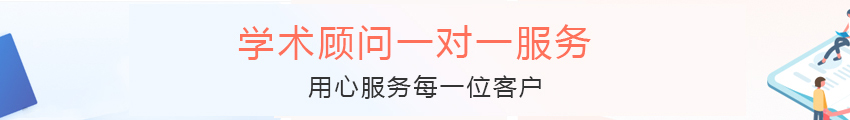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美国摄影师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在1889年曾拍过一张名为Sun's Rays的照片——黄昏被百叶窗切割,均匀、细长的光影伸出古老的手臂,悄然笼进房间; 一位母亲正在写信,她的眼神低垂、专注,不受外物侵犯,黄昏的光影打在她平静无波的脸上,似乎把时间也切割成了条纹形; 只有笔尖和纸页之间窸窣有声,这响声和光线一起,继续切割着桌布上的孩童相框和钉挂在花色墙纸上的多张人物肖像照。 ——掩埋于时间深处的人脸神秘、深邃,仿佛身处小径分岔的迷宫,隐隐散发出关于人间的消息。 就像李约热在《到乡下吹吹风》里写的:“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去仔细端详一张人脸,人脸上的晨昏,肯定比大雨落在阔叶植物上面惊心动魄。 ”这篇可用作刚刚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集《人间消息》自序的散文,恰好道出了李约热小说中深藏不露的人物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个个解不开的连环死结,人性的真实与荒诞都隐藏在小径分岔的日常生活中,其诡异程度与“野马镇的人生”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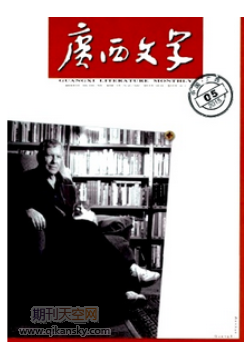
野马镇的影子
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提到过这样一种观念:“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 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 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这种观念同样适用于李约热的小说。 如果说世俗生活是一个庞大繁杂的迷宫,那李约热的小说就是一条条分岔的小径,只是主角由“时间”换成了“人”。
《村庄,绍永和我》是《人间消息》的第一篇小说,仿佛从一个坍缩的黑洞传来,连接着两端的无边旷野和烟火人生。 对李约热来说,旷远的是城市,充满烟火气的是野马镇,作为开篇小说,《村庄,绍永和我》承载的,恰恰是作者内心那个小径分岔的关键点。
村庄是单位派“我”去扶贫的驻扎点。 从表面上看,它和我的故乡“野马镇”大相径庭——远看清新迷人,近观肮脏混乱,不仅野性不足,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沉麻木,“生老病死过于波澜不惊”。 在村主任的叙述中,十几年前的一起群体中毒事件像一把尖刀,层层剥开了这个村庄的真面目。 老实巴交的海民因为“农药中毒”被老婆美雪深夜送去医院,抢救回来之后庆幸捡回了一条命,就请朋友们来家里喝酒吃饭。 谁知道这一顿酒饭又把七个朋友直接送进了医院,甚至把冠远的儿子忠发送进了棺材。 后来才发现,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海民的酒,他不小心把断肠草的根当成八角树的根泡在酒里,在无意识中,他和七个朋友,都成了集体中毒事件的受害者。 ——在这件事里,海民是无知的,七个朋友是无辜的,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偶然性的忽略,更是因为这个村庄的孤独,那些在黑夜里默默发生的生离死别,让整个村庄沉浸在人间的悲凉心事里,却以连环死结的方式,锁住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渠道,只有深夜里那束野兽眼神一样划破黑暗的摩托车光柱,隐隐透露出生死的悲壮。
在“村庄”这个自闭的大圆环里,绍永的故事无疑是另一个小圆环,贯穿着村庄的“孤独”迷障。 作为村庄的年轻人代表,绍永选择了逃离,只是逃离的成本太过巨大——大学毕业,选择传销,窝点被警察端掉,被遣送回家之后,竟割脉自杀,所幸被救下。 绍永的自杀未遂事件,本来只是村里无数孤独往事的其中之一,但它却以一种交错会合的方式,和“我”有了一次交集。
“这个村庄的每一家每一户,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消化。 每个苦难都有来路和归途,像雨融于土地。 ……这个孤独的人间。 我以为自己已经怀揣这个村庄的心事。 如果把这个村庄当成一个人,那这个人也可以是我。 ”
在这篇小说里,“我”离开“野马镇”已经很远了。 作为一个常年生活在城市里写小说的人,曾经在野马镇撒泼打滚、既傻气又讲义气的“我”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我”和自闭的绍永一样,和这个沉默的村庄一样,“不再关心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别人的伤痛、衰败也熟视无睹,不再愤怒,也不再焦虑,心如死水”。 而此次的下乡扶贫,对“我”来说,实际上是追溯“野马镇”野性人生的种种挣扎,是寻求一种人间对话的努力。 正是这种挣扎和努力,促成了“我”和村庄、和绍永的交集。
然而,对话是困难的。
“绍永躺在床上,裹着红色的棉被,背对我。 我只看见他的头发。 他床前摆着一张桌子,一台崭新的台式电脑立在床前,电脑的包装盒子扔在房间一角。 可怜的瑞明,为了讨好儿子,给他买电脑。 绍永现在,只跟电脑亲。 ”
由“野马镇人生”延伸而来的心路历程,和瑞明父子间的血缘亲情一样,在冷酷自闭的绍永面前,竟然也是一文不值、毫不动心的。 但此时,突然出现了小说中第一次的“小径分岔”——老人瑞生三岁的小孙子出现了,天真无邪,喊着“爸爸我爱你,爸爸我打你”的话跑到绍永床前,用指头摸摸绍永的头发。 实际上,绍永并不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母远在广东打工,孩子作为留守儿童,常年和爷爷瑞生住在一起。 对“孤独症患者”绍永来说,孩子的留守生活是能够激起他内心的波澜的。 ——但是,冲击力还不够。 李约热小说艺术的高明之处在此尽显无疑,小说在层层递进的心理铺垫中逐渐走向高潮,村庄、绍永和我的“孤独圆环”也即将在偶然出现的孩子身上得到交集,但是,他按下不表,他要等着一个能够猛然打开绍永心结、震撼人心的“偶然性”事件的到来。
当天夜里,在“我”第二次探访绍永被拒绝之后,“我想去瑞生家看看。 随便跟瑞生聊点什么,打发这个夜晚”。 ——“偶然性”像最诡异的连环迷宫,深藏在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此时,第二次的“小径分岔”出现了。 “我”看到了孩子落在切猪菜机器旁边的三根断指。 当我怀揣断指踢开绍永的房门,喊他带去县城医院时,绍永那张面无表情的脸终于改变了——“一张惊恐的脸”,不仅如此,在赶去医院的山路上,绍永第一次跟我说了话:“我们还能快点吗? 我们还能快点吗? ”这句发自内心地对孩子深切关爱的话,终于打破了绍永和“我”之间的沟通怪圈,在这个孤寂空旷的乡村之夜,最终以“野兽的眼神”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
李约热正是用这样一个寓意深长的开篇之作,展示了“野马镇人生”在另一处人生境遇中的分岔和延展,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小说旅程中,小径分岔的“野马镇人生”还会有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可能性。
错位人生
李约热不同于先锋型作家,为人类的普世生活在文学上的表现做各种新奇的写法实验; 他对现实有一种奇特的信任感,更专注于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新的发现,进而将切割生活的方式发展成新的写法。 这种“发现”与“写法”之间的磨合,体现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 如何将“发现”进化为“写法”,正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点。
作为《人间消息》的第二篇小说,《龟龄老人邱一声》紧紧承接着《村庄,绍永和我》,对“野马镇”进行了一次意义特殊的重返。 或者说,“野马镇”的分岔小径在途经中转站《村庄,绍永和我》之后,竟然出乎意料地将小说的路径转回了野马镇的烟火人生中——《龟龄老人邱一声》《情种阿廖沙》《幸运的武松》《你要长寿,你要还钱》,小说集里的四篇作品,分别从乡情、爱情、友情、亲情的角度,重返了野马镇的精神源头。 而《龟龄老人邱一声》,更因其多声部叙述和错位并用的写法成了典型。
“邱一声是我们野马镇年纪最长的老人,7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阿牛跌河死了,从那时起他开始失忆。 野马镇的人喜欢跟他对话,他们问他今年高寿,他永远都这么回答:今年70。 ”
孤寡老人邱一声,因为自己的长寿和失忆,竟然活成了野马镇的骄傲。 在这样一位阅尽世事的老人面前,野马镇的人们彻底放下了自己的面具,趁着轮流照顾他的空当,把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人间浮世绘”呈现在他面前。 从屠夫董志国、菜贩子蓝伏龙,到拿邱一声当消遣的阿明、阿卫、阿三三兄弟,拿邱一声当受气包的董志国老婆阿珍、蓝伏龙老婆阿香,拿邱一声当“神”供奉的阿亮、张权老婆阿锦……每个人都把自己长年积压在心底、不敢对外宣泄的痛苦以各种方式发泄在邱一声面前。 此时的邱一声,用“上帝”的形象将野马镇每一个人的苦难尽收眼底,却不予置评。 冷静的旁观视角将众人的苦难层层叠加,最终烘托出一个个虽受尽凌辱但仍坚韧顽强的“野马镇人生”。
这种多声部叙述的写法,是李约热的长项。 早在2005年的小说《涂满油漆的村庄》,李约热就已经用得炉火纯青——那些轮流在韦虎的照片前喃喃自语的加广村村民:烧石灰的韦金多、爱喝酒的马亮、捡垃圾的钱飞、伤残老兵刘广大、想自杀的精神病人乜春……都以个性十足的自述构建了一个伤残与傲气并存的“野马镇人生”。 到2014年的长篇小说《我是恶人》,多声部的叙述更是把野马镇的千人千面贯穿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那么,这种多声部叙述的写法到底源于什么样的生活呢? 在我看来,它源于李约热对野马镇精神源头的审视和概括,即“寓言性”。
加广村是个寓言,野马镇也是个寓言。 不同的是,早期的加广村是以虚构的标新立异为主的寓言:《涂满油漆的村庄》是一个建立在全村人的苦难底色上的“假村庄”,在现实中不易遇到,但它在虚构上的精彩和合理让整篇小说充满了意料之外的曲折和精彩。 后来的野马镇是从现实的平凡与偶然中深挖出人性的寓言:长篇小说《我是恶人》是死者马万良的回忆之书,寓言般屹立在活人的记忆之外,人们早已忘记了逝者的哀痛,依旧在现实中上演着巧取豪夺的“恶人”闹剧。 所有的情节和场景都平实得如同我们身边的生活,没有另类的事件,没有突兀的故事,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平凡中,“恶”却以不动声色的姿态贯穿了整个野马镇。 ——此时,多声部叙述的写法将野马镇的人生横向铺开,在众说纷纭却又贯穿一致的精神源头中,完成了对“寓言”的刻画。
野马镇的每一张脸,都像刀子一样在李约热的心里凿成石刻,有悲怆的阴影和底色。 同时,根植于野马镇人精神深处的那种模棱两可的世俗观念,对人情世故“踢皮球”的滑稽冷酷,是更接近庸常生活本质的一种“恶”。 是非对错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里,没有人是无辜的。 如果不把这些交错的悲欢写在纸上,它们迟早要把整个心堵成石墙,彻底和外界断了音讯。 正是对隔绝的恐慌,让作者在游刃有余的多声部叙述写法之后,用了能引出对话的“错位”写法。
“第一次进他家门的时候,我是死刑犯李永强的儿子李谦,第二次进他家门的时候,我是他的儿子阿牛。 ”
生死之间,由于时空的错位,互不关联的四个人,忽然间拥有了共同的秘密一般变得亲密无间起来。 于是,在一个点着煤油灯的寒夜里,往事交错庞杂,一一重现:邱一声紧紧握住死刑犯李永强儿子李谦的手,哭诉自己跌河死的弱智儿子阿牛; 李谦坐在邱一声的身边,眼眶发热地对着虚空中的父亲喃喃自语; 在大雨中默默告别父亲缓慢走向河边的阿牛,临刑前紧闭双眼不再看儿子一眼的李永强,在呢喃的往事中一一浮现。 此时,悠长世事中的四条毫不关联的小径,终于交错纠缠到了一起,产生亦真亦幻的诡异感,仿佛人鬼不再殊途,而是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 在不断的碰撞与呼喊中,对话与和解才会异常惊心动魄。
最后,龟龄老人邱一声终于在与“阿牛”重逢之后心满意足地死去,李谦作为邱一声的“孝子阿牛”,永远留在了野马镇。 那块为邱一声立的墓碑,仿佛也是李谦在心里为自己的父亲李永强立的纪念碑。 两对隔阂深重的父子,在死亡面前达成了彻底的和解。 小说写到这里,多声部叙述、错位写法如同世事花园中不断交错分岔的小径,也在殊途同归中让整个野马镇人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从而真正实现了人间对话。
旷远的城市
对李约热来说,城市是旷远的。 尽管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内心却依然有着浓重的荒芜感,仿佛远在天边的野马镇才是充满人情味的烟火人生,而城市,尽管近在咫尺、光怪陆离,却始终是一片野地。 这种体悟,是我阅读《南山寺香客》《美人风暴》《人间消息》《二婚》四篇有关城市人生的小说感受到的。 这种荒芜感直接将李约热的写作轨迹往背离的方向引去。 如何做到内心力量不流散,对他人有悲悯,事关内心的重塑。 于是,小径分岔的“野马镇人生”,此时以另一种姿态,朝荒芜的城市生活蔓延开去。
“佛看得见人间,未必看得见每一个人。 ”
南山寺的佛,总会把尘世中各种各样的人吸引过来。 比如:身陷“驱逐之年”的中年知识分子李大为、向李大为引荐“李师”的瞎子摸骨师、盲目崇拜佛祖的出租车司机、要在南山寺搭建房子的夫妻……在人世浊流中挣扎的蚁群,遥望于云端双手合十的佛祖之时,或多或少都会对出世的静穆与逍遥心生向往吧? 这些在平行世界里各自生活的“可怜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山寺的“李师”,也许永远不会相遇; 就像小说里写的,每当“南山寺的钟声在前方响起,他看见鸟群从树木上腾空,朝钟声响起的地方飞去,好像听懂某种召唤一样”。 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位偶然间出现的“李师”而有了分岔和交集。
“李师”究竟是何许人也?
“循着男人的手指,在‘闪电’的一端,一个穿和尚服的人飘在路上。 有风,所以看起来像飘。 还有五十米,李师就哈哈哈哈地笑了:‘这个瞎子,又给我介绍香客来了。 ’”这样的“和尚”,潇洒、和气、爱笑,和李大为想象中伴随着青灯古佛、庄严肃穆的“高僧”一点儿也不一样。 不仅是看起来不一样,相处起来更让李大为吃惊。 他们不谈佛,只是喝茶、聊天。
“亭子正中央摆着张石桌,桌子上方吊着个大篮子,李师摘下篮子,里面装有烧水用的开水壶,他取出水壶,把篮子放在一边,揭开水壶的盖子,从里面取出小紫砂壶和茶杯摆在石桌上,熟练得就像魔术师从百宝箱中取物件。 之后,低头弯腰,从石桌底下拉出一个炉子,又拉出一小捆干柴,烧茶用的家伙都齐了。 ”
小说里的对话很多,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这种接近于白描的动作描写。 没有铺张的形容词,没有过多的感慨,凡尘俗世仿佛在静默中远去,安稳自在的精神在静默中抬头,并自由生长起来。 小说里的和尚“李师”,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和大家一起煮茶聊天,关心尘世中的父母,关怀想念病儿的年轻夫妻,也理解不信佛、只喝白开水的李大为。 他认为:“所有的规矩,都应该为众生而立,人心都是肉长的,和尚也一样。 ”正因为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和尚,让来南山寺的香客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一种宽厚的理解和善待,明白“佛看得见人间,也看得见每一个人”。
这种入世的佛家观念,打破了僧俗两道的壁垒,也让在城市中挣扎的人们有了心灵的皈依之所。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世俗和精神之间的纠葛。 长久以来,世俗对精神的误解到了憎恨的地步,很多时候是因为精神高高在上。 所谓的“恃才傲物”,实际上和“财大气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人们会因为有钱人炫富而心生厌恶,那么那些因为精神和才华的优越而蔑视凡俗的“桀骜不驯”者,也很难不招致愤恨。
小说中“李师”这个人物设定的关键处就在于,他把自己放在了“箭靶”的目标位置——也就是说,在展开人间对话的过程中,只有从自身出发,让自己置身于世俗,才有可能藏身人群,从而在他人身上抵达自己。 这种具有强烈指向性的孤独和悲悯,让世俗中的众生、让所有俗人俗事的苦痛往自己身上洄流:不管是野气纵横的野马镇,还是隐忍苦痛的人间村庄,或是迷惘自失的城市人,在各个平行时空中并行分岔的人生路径,终于能在一种宽厚的悲悯精神中达成和解; 人间对话也因为丰富了世俗与心灵的层次感,而最终抵达了行动。
小说的最后,李约热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阐释了这种“行动”。
一个初为人父的男人,看着自己刚出生的、身患先天性脑积水的儿子,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与迷惘。 他甚至第一时间乞求医生把他的孩子处理掉。 请求无果之后,他和同样痛苦的妻子打算把孩子扔给远在几百里外的宣城福利院。
“深夜两点,女人给孩子喂最后一回牛奶。 男人下车,狗跳了起来,在他脚边嗅来嗅去。 男人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取出装孩子的竹篮提到车门边,铺上毛毯。 男人打开车门,从女人手中接过孩子,放在篮子里,再盖上小棉被。 男人提着篮子往福利院方向走,那条狗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 ”
这一场人间离别,没有对话,没有交流。 表面上冷酷无情的父母用无言的行动给孩子做着最后的准备。 那条紧跟男人的流浪狗,勾起了读者绝望的幻想,似乎后面还会发生更加残忍的事情。 果然,丢弃了孩子的父母听到了打狗人的喊声:“叫你吃孩子! 叫你吃孩子! ”男人赶紧推门跳下车,朝孩子飞奔而去。 结局出乎意料,实际上那条流浪狗并没有吃孩子,它只是想咬住篮子把孩子拉回给这对“无情”的父母,却因误会而被人打死……
寂静的深夜,只有男人的话语在冰冷的回忆中流淌。 这场道德与生存的拉锯战,最后在李师以退为进的劝诫中达成和解。 “我们一家三口,想在这里重新开始。 不管以后有多难。 ”男人最后对李大为说的这句话,让整篇小说结束得干净利落、掷地有声,仿佛所有的路途,都可以在千回百转之后归于自身; 而小径分岔的“野马镇人生”,在历经了苦痛、打击、自闭之后,也都在战胜自我的人间对话中,用行动达成了圆满。——论文作者:刘景婧
相关期刊推荐:《广西文学》(月刊)创刊于1950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容详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强、信息量大,众多的栏目设置,广西文学公认誉为具有业内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其中主要栏目有:小说_短篇精制、小说_微篇妙品、诗歌_诗群绿风等。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