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15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现代主义及其理论批判构成20世纪80年代文论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伴随着双重焦虑:被延迟的现代化焦虑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焦虑。由此造成的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
摘要: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现代主义及其理论批判构成20世纪80年代文论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伴随着双重焦虑:被延迟的现代化焦虑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焦虑。由此造成的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内在张力结构,成为中外学者探讨中国现代主义的基本二元论框架。这些二元论架构带来了启示与盲点,将性别维度植入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在全球本土化视野中洞察现代主义的权力关系及其性别修辞,即可在揭示现代主义文艺隐含父权无意识的同时,尝试建立现代、民族与性别互动对话的三维理论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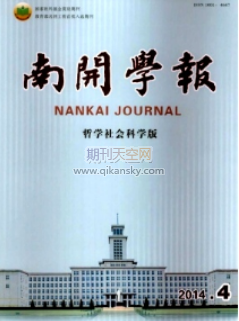
关键词:现代主义;民族寓言;性别
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一方面,由于现代主义与西化、世界化关系密切,使之在激切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往往作为一种进步文艺形态而具有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诉诸内面性的个人主义诉求,又与现代中国的感时忧国传统相扞格,使之不得不屡受质疑。这个矛盾状况导致现代主义文艺实践在现代中国时断时续,相关评价也往往在肯定与否定的两个极端摆荡。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没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现代主义的位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艺中的缺席,社会主义文艺的超现实主义面向,使之亦具有区别于西方经典现代主义的另类的现代主义特征,但在日后的文艺批判中,却被作为反现代的落后文艺而受到否定。
一般认为,经典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改革开放的中国融入西方世界、重启现代化项目的文化表征,现代主义文艺及其理论生产,由此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建构的重要内容。纵览几十年来围绕中国现代主义展开的理论建构,就会发现“民族”与“现代”所构成的相反相成的二维结构,是中外学者展开论述的基本二元论框架,无论是渴望现代论、民族寓言论、中国主体论,都在这个二元论架构下展开,并由此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霸权性研究范式。实际上,在民族与现代、国家与个人的二元架构之外,性别作为奠基于社会实存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艺的结构性内容,但却在既往的理论生产、文化诠释中隐而不彰。将性别作为第三维度介入中国现代主义的理论生产,建立一个由现代、民族与性别构成的三维结构,有可能是重估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再造本土研究范式的有效途径。
一、现代主义与民族复兴
1987年12月10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比较文学学会联合在香港主办了“第五届国际文学理论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①,出席此会的海峡两岸和海外学者、作家和批评家有五十多人,大陆的有郑敏、袁可嘉、谢冕、李陀、黄子平、季红真、许子东、吴亮、钱中文、王宁、王安忆、刘索拉、顾城等。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研讨会上,大陆和海外学者在一些基本议题上存在一定争议:一是关于女权,大陆女作家王安忆和刘索拉以不同方式发表了一个类似“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宣言,这让一些海外学者非常不解。②遗憾的是,这一争议并没有延伸至大会的中心议题——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讨论一开始就缺少一个必要的性别矢量。一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情感态度:周蕾对谢冕论文《现代主义:中国与西方》中的“感情结构”不以为然,认为其理解现代主义的方式与现代主义正相反。对于现代主义的情感态度问题在后来的讨论中得以充分展开,海内外对现代主义理解的差异与错位,也使隐藏在现代主义论述背后的不同的文化政治得以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港的现代主义研讨会值得关注。
谢冕论文的主要观点包括:现代主义在中国从“断裂”到“对接”的变化,源于“艺术反抗主义”的诉求与“重返世界的愿望”;中国文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有其历史契机;现代主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继承,仍然是“中国式”的。③“中国式”指的是“特殊的本土经验和感受”,是“文革”造成的破坏性的震惊体验。在谢冕这里,(西方)现代主义主要被看作一种文学手段和书写方式,是文学的形式与结构问题,这种对现代主义形式与内容进行的分离式接受法,在当时相当普遍。当然,分离式接受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真的认为二者可以分离,而更多是对曾作为冷战禁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达的现代主义的辩护策略,这种策略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思想的体现。
虽然论文题目将现代主义明确置于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架构内,但谢冕的意图却不在于呈现本土/中国与异域/西方之间的对抗性。(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文学可能带来的文化主体焦虑,此时远不及告别“文革”、走向“新时期”的愿望更为迫切。现代主义论述的中国/西方的外部二元架构于是被置换为“文革”“/新时期”的内部二元架构。虽然他也提到了现代主义的“中国式”与“本土经验”问题,但“本土”诉求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而非对抗(西方)现代主义,谢冕“中国与西方”架构内的现代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主义思想,而中国经由努力可以达至这种普适性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中国与西方》体现了一个诗评家的独特气质,饱含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澎湃激情。
但正是这种弥漫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中“被延迟”的现代主义焦虑与“走向世界”的新想象,引起了评议者、时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周蕾的关注,她敏感地意识到论文在“客观结构”外,还有一个“感情结构”。就此,她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要用‘回归’、‘重返世界’这样的观念去形容中国的现代化呢?要是‘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应该发扬光大的意义)是多元化、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思维,那为什么在中国文学重新开始实行这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看似非常单一的概念去理解它,把中国文学说成‘弃儿’找到家一样?这种单一的感情的结构,与‘现代化’是不是相反的呢?”①周蕾质疑了谢冕对现代化、现代主义的理解,认为“单一的感情结构”体现了对现代化的单一化理解,而现代化在周蕾看来则是多元的。周蕾对用“单一的感情结构”来理解现代化的警惕,对中西看待中国现代化的两种不同情感方式——“弃儿重投母亲怀抱”与“老处女最后不得不打开”——的并置与质疑,约略看出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后殖民立场。
从小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生活在境外的美国学者周蕾自然难以理解内地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这种“情感结构”,正如身处现代主义/现代化焦虑中的大陆知识分子,也很难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感情结构”。不过,周蕾只注意到内地学者一厢情愿接受与追随现代主义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追随和接受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民族复兴的诉求。从徐迟的《现代派与现代化》、高行健的《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到李陀的《现代主义与寻根》,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从不缺乏民族主义的内核,只是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是现代主义得以在中国流通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尽管不无误读成分,但周蕾对现代化的冷静态度与批判立场,却有可能警醒局内的内地学者,这可能是周蕾短评与谢冕论文后来同时刊发于《文学自由谈》的原因吧。
现代主义接受中的“情感结构”后来在许子东的《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深入分析。他看到中国评论家很少考察现代主义不同“派”之间的差异,而更关心现代主义与“我们”的关系。这个“我们”,在许子东看来,至少包含(阶级)政治、时代、民族这三种立场,只是各有侧重隐显,构成极为微妙的文化景观,而民族文化的危机与使命感,则是倡导者的重要合法性来源。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就被“我们化”了,无论反对、保留还是支持现代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参与着现代主义的“我们化”过程。将现代主义“阶级化”在“新时期”已是明日黄花,而“更坚定更热忱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才是一种更顺应人心的“情感愿望”。民族主义的情感愿望贯穿于中国现代主义实践的始终,许子东认为,早在1982年“四只小风筝”通信时,李陀在赞同冯骥才热情呼唤现代派的同时特地将“我们”的“现代小说”与“洋人”的“现代派”之间划了界线,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现代主义”与民族文化更多结缘。②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的是对中国现代派作家影响最大的袁可嘉。还是在这次会议上,袁可嘉提出并阐明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性质:“应当是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相对应,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为社会主义(而不是最表面意义上)、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沟通的,是与民族优秀传统相融合的,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现代意识(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技巧和风格。”③袁可嘉的“中国式”现代主义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风格与意识等的调和。但如何混合、怎样实现,这种“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是否还是现代主义呢?于是,在各种提倡“中国式”“我们化”现代主义的同时,是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还“不够现代主义”的抱怨与批评。香港会议上,季红真在比较中国现代派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④这呼应了国内已经出现的“伪现代派”说法。黄子平则分析了“伪现代派”批评与“纯现代派”要求背后的悖论,认为这是试图剥离自身的体验和文化以迁就或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完整性的做法,那些把现代派文学营养吸收更好的作品,恰恰不在技巧,而在于对人生、世界的某种共通的体验。①黄子平讨论现代主义的方式,在许子东看来,“标志着中国评论界对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种冷静的专业研究态度的出现(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每种意见首先意味某种情感愿望)”。②
于是,许子东一方面肯定现代主义“我们化”过程中汉民族的民族文化本位是一种更顺应时代的情感愿望,一方面又警惕“情感愿望”在“我们化”西方现代主义会产生的问题:“‘我们’当初曾经那么急切地消化改造了西方现实主义这种‘异质’文化,要求立刻‘为我所用’,结果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精髓既未能在当代中国(从‘左联’到‘文革’)扎根,而民族文化失落感也未真正消除。有不少人都认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次复兴汉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机,机会与二十年代颇相似。正当现代主义确实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之时,我想应冷静观察下去:看看这种‘我们的现代主义’,是否又会变为一种新的‘我们的现实主义’?”③许子东的隐忧并非没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式”“我们化”的现代主义,既是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尘埃落定,也是其衰落的开始,先是寻根文学思潮对民族性前所未有的强调,后是“新写实”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曾经被认为是搅起语言革命、叙述革命、形式革命的先锋文学,则被认为是“时间与地点的缺席”,是“‘西方主义’的症候式表达”。④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关于现代主义“要不要”“好不好”“真不真”等论争,体现的还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普适性理解,虽也在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下,但出于“被延迟的现代性焦虑”,外部的中/西空间区隔转化为内部的“文革”“/新时期”、封建/现代的时间性划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现代化的渴望与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激情并存,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对抗性处于隐在状态。但随着80年代的终结,理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与未来的期冀(中国向何处去)也开始分化,一种新的评判现代主义及其文学实践的框架开始浮现。——论文作者:马春花
相关期刊推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南开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55年,是新中国创刊较早的高校文科学报之一,为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刊发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性文章,注意反映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的新成果、新信息,鼓励创新,支持争鸣,以深刻厚重的学术内涵和严谨朴实的编辑风格。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