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1-05-0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280次
摘 要: 摘 要:视觉符号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社会建构的主体。通过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以傈僳族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我们发现这些处在不同表征传统之中、按照不同的生产逻辑制作出来的图片序列,呈现的远远不只是被拍摄者的形象和故事,而是由拍摄者、传播者、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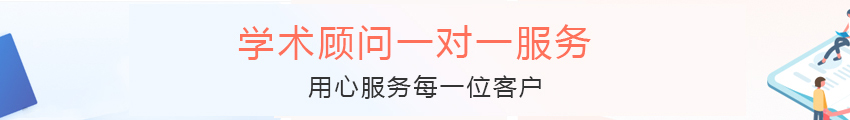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 要:视觉符号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社会建构的主体。通过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以傈僳族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我们发现这些处在不同表征传统之中、按照不同的生产逻辑制作出来的图片序列,呈现的远远不只是被拍摄者的形象和故事,而是由拍摄者、传播者、阐释者所构建出的文化表征。摄影作品所塑造的现实,也不仅仅是再现了被拍摄对象的现实世界,更多的是技术美学、国家观念、变迁话语、传播机构所塑造的,对现实产生持续影响的媒体世界。

关键词:表征理论;框架理论;傈僳族;摄影作品;视觉人类学
文化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群体不断适应环境并调整自身,从而建立起来的复杂机制。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经历接触、传承、濡化、变迁等种种演变的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带、文化圈、文化层等,并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结构与形貌。文化也可视为动词,这就意味着文化是意义建构、群体塑造和文明传承过程中的一部分。它是建构群体行为特征甚至是思维方式的手段,也是塑造社会意义网络的历史进程。其中,事物、行为、符号和概念图示都成为可被感知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帮助人们认识周遭世界,也帮助人们将具体的存在和抽象的概念用符号联系起来,从而为整个世界赋予意义。因此,透过文化现象和文化表征,观察者能渐进式地发现、理解文化意义得以产生的机制。
亚里士多德曾将所有的艺术、语言、视觉和音乐都界定为再现,即表现的形式,而且将其视为确定的人类行为。人类最清晰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表征的不断创造和再创造。①因此,文化表征是传播中的文本,是建构中的历史过程,是不断塑造人的环境。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集中于视觉和语言符号上。比如在大众文化如何建构了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的分析中,霍尔着重阐述了话语权力、身份认同与表征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文化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群体认同。这一点在大众化的视觉媒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②彼得·汉密尔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5 年间的纪实摄影师的研究回应了这一论点,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平民主义范式”,即不同摄影师的作品在题材、方法、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体现出对生活中的艰辛和矛盾的直面对视,又包含了对团结精神和温情主义的强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动荡分裂的伤痕社会中,构建了一种新的法国社会形象和法国身份,成为“法国性”的重要表征。①
在当下的媒介化社会中,视觉符号的生产和接受、编码和解码已然成为人们沉浸的媒介世界中的日常状态和生活实践。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著作,表征理论延续结构语言学的传统,讨论文化与话语、意义与表征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电影、摄影、电视、广告等视觉媒介如何使用技术的客观性来为形象建构提供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未必经得起质疑,霍尔以及表征研究的继承者们就为我们揭示出人、媒介和真实世界之间的遥远距离。
显然,事物的意义就是在事物与符号的关系中产生的,而对视觉符码的生产和传播,则是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与傈僳族相关的新闻摄影、摄影专题和艺术摄影三个不同的摄影类别,来简要勾勒视觉媒介通过何种方式呈现了什么样的傈僳族形象。
一、傈僳族的文化认同与群体表征
在唐代到清代的族群迁徙史中,傈僳族并非政治含义明确的“少数民族”,而是以形象不甚明确、样貌不甚清晰的状态游离于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由于长期以来与中央王朝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其认同更多的是随社会情境和边界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当傈僳族面临环境资源压力或战争压力时,其群体常常有相当灵活的身份转变。另外,历代王朝对傈僳族的统治维持着一种间接和有限的管理,比如主要通过土司制来完成对整个地区的管控而不是直接针对族群人口的控制。清代中期开始,中央王朝力量在西南边境地区不断深化,加上汉族人口随着迁徙的过程日益增加,使得族际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发生大规模的抗争。而在抗争过程之中,傈僳族反而极大地增强了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其后,英国在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进犯缅甸和怒江,直接引发了滇西各族人民的英勇抗争。尤其是怒江一线的傈僳族、景颇族反抗,迫使英政府承认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属于中国。抗日战争中,他们也共同反抗入侵滇西的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认同得以凸显和强化。解放后,在开明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影响下,傈僳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得到强有力的建构。
在群体的文化认同方面,傈僳族的创世纪的故事将灾难记忆、兄妹传说、族群关系传说、自然认知、资源分类等多种元素整合在一起,通过亡魂回归祖先家园的隐喻式的行走路线的详细描述,来强化自身归属,并在葬礼等重要仪式中代际相承。这些因素共同赋予了傈僳族的自然和文化世界,同时也提供了群体生存所必需的价值和意义。在傈僳族普遍存在的迁徙传说中,族人从“石头月亮”出发,沿着怒江和“太阳落山的方向”不断迁徙,根基性的身份唤起原初的集体记忆,迁徙叙事则强调了延绵不断的群体身份。此外,傈僳族也通过不断创造的传统来构建自身身份。比如在保山和腾冲一带的傈僳族刀杆节,就是通过“上刀山下火海”的象征仪式,来表述傈僳族勇敢善战和保家卫国的群体精神,并把自身和明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边界拓展过程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完成正当性的诉说。至此,斯图尔特·霍尔详细讨论的群体通过讲述“我们的”故事来演述自身身份,通过符号和表征来组织行为和观念的理论归纳,也在傈僳族的文化表征中得以清晰看到。
二、形象的框架:新闻摄影中的傈僳族形象
框架理论发源于认知研究,受到认知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推动而得到验证。早期研究者格里高利·贝特森既是对视觉人类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类学学者,也是透过影像来进行社会心理和人格研究的学术奠基者。他认为,从社会事实、集体表象等宏观结构和个人的认知、情感的体验、习惯的获得之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化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就是社会性的认知基模或者认知框架。透过濡化的过程,社会认知框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成员。①欧文·戈夫曼也视之为发生学机制,认为“框架”是人们对社会事实的进行解释的基本架构,也是促使个体转化得以产生的前提。框架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经由内容分析而变得普及,比如新闻题材的选择、重新组织和编辑,不只是新闻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针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框架,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时代变迁,不断变化其类目。②社会制度、文化形态、机构角色、受众构成等因素会对框架的结构产生影响。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上,有研究者尝试通过梳理纸媒文字报道中的框架,来分析报道背后的形象建构方法。比如关于少数民族的制度、内容、法律、道德等报道,既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也是按照一定之规形塑了人群的基本样貌。它们不只是新闻修辞的方法,也是形象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笔者通过慧科新闻数据库进行初步的检索,以“傈僳”和“傈僳族”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搜索,同时辅以全文搜索来补充某些类别的不足,一共收集了傈僳族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十一年间包含图片的报道材料450篇。整体上看,关于傈僳族的报道数量偏少。而在这十一年间,虽然传统媒体逐渐式微,但关于傈僳族的报道在这十一年间却有大幅增长。网络媒体,例如中国新闻网、央广网以及各地政府网等对傈僳族的报道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状态。从2010年起,关于傈僳族的报道数量增长较多,尤其是配合地方发展的系列活动推出后,往往形成报道数量的小波峰。这种变化说明了形象表达的密度和地方经济开发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其中的大量被转发和复制的纸媒图文报道为主要内容,辅之以媒体客户端上的相关新闻图片,来说明对傈僳族形象的传播中大众媒体在傈僳族形象上的建构模式。
通过对数百张图片的内容分析,笔者发现在图片的内容上,以呈现传统民俗事项、民间工艺美术制作、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民族地区政策利好、人口和经济发展状态、传统文化和优秀品德、民族地区美景和民风民俗、参与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活动等为主。相关图片多来自报道现场的采集,以文配图的形式来体现现场的气氛和人物,从而为新闻内容的描述提供证据式的图解。相应地,傈僳族的形象也随着报道框架的变化出现不同的面向,比如民间文化持有者、民族团结维护者、政策法规受惠者、扶贫发展受助者、传统文化坚守者、优秀品德维护者、旅游目的地接待者、乡村进步建设者、经济活动参与者等形象。
与之呼应的视觉表征也有迹可循。首先是针对某些特定内容采取相当一致的画面形式。比如香格里拉市的阔时节文艺会演,④或者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成立30周年庆典报道⑤。象征民族团结的舞蹈和圆形构图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的视觉形式,用来表达人们欢聚、和谐共存、族群共生的意念。由于其形式感较强,这种构图也成为一种常用的镜头形态,来隐喻欢聚一堂的状态。这些照片中,具体的人物并非表达的重点,反而是服饰的多样性和圆形构图的完整性成为最重要的视觉图式,用来表达民族和谐的抽象理念。再比如,大量的摄影报道呈现了参与到国家政策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物形象,不少图片反映了党和政府、机构等对受助者的关怀和帮助。在这些图片之中,上述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通常被没有辨识度的日常着装所替代,环境,尤其是生产劳动的环境、人物的动作和面部特征往往得到强调。通常呈现出几种视觉样态:一是人物的形象和相关材料的证据式的展示,常常通过不同景深的视觉元素来形成关联;①二是对参与者自然状态的写实性描述,常常用抓拍的方式完成;②三是历时性变迁的对比性呈现,用写实的镜头呈现如聚居地的新旧对比,生活条件的好坏对比等;③四是国家建设者、各行业典型人物、发展参与者的表意性呈现,往往用较为特别的拍摄角度来表达,并大量使用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的符号,比如溜索、弓弩等。④另一个较多的类型则集中强调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性和民族地区人民的热情态度。这是因为随着绿色发展和旅游开发的兴起,旅游目的地建设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增长点。
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和独特文化的魅力往往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来源之一。与此对应的少数民族景观多为村落和自然景观,同时凸显差异化的风俗习惯,对应的人物形象多为身着民族盛装,秀美姣好的女性,从而建构起一个对外来者颇具吸引力的空间。⑤通过特写镜头描述少数民族的服饰细节、身体标志和面部特征的人物摄影作品,通过现场的气氛调度来强调神秘性的环境肖像作品,通过选择“决定性瞬间”的光影的风光摄影作品等,都被用来完成“熟悉中的陌生感”塑造。⑥在这里,文化要素被提取为抽象的符号,作为核心部分在图片中被强化,并透过上述视觉框架在大众传播中不断地被传播和被观看,同时内化为我们表达他者的常用方式。
三、视觉表达的前台:专题摄影中的民族符号
纪实类的专题摄影作为一个类型,其社会功能一直被强调,比如为社会变迁留下视觉性文献,为日常生活赋予价值感和合理性等。⑦纪实摄影被认为能够推动社会改良,能够作为参与社会工作的工具为弱势群体争取发声的机会,甚至能够直接参与社会公益的进程。⑧除此之外,纪实类摄影立足于社会事实,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视角或者文化传播的方式。
本节以《中国日报》(英文版)的图片报道“中国 56 个民族的历史照片”(Historical photos of 56ethnic groups in China)为材料,来分析这些经由专业对外传播机构的筛选和编辑,以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为表述核心的影像组合,呈现出的少数民族形象特征。通过媒体机构的汇集、筛选和重新编排的不同民族的图片,加上详细的图片说明,成为传播民族和谐理念的统一整体。
《中国日报》(英文版)旨“在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A Voice of China on the Global Stage),定位为面向全球受众的窗口。整个版面由互动式的网页构成,页末表明“特别报道”,强调图片为主导的表达。页面采用集锦式的呈现方式,主页面直接由56张图片的缩略图组合而成,点击缩略图后的每一张照片下分别附图片说明。① 从主页上我们就能直接得到一种集锦式的印象,不同的地域特征,不同装扮的各民族人民或族群成员,文化汇集在一起的视觉样态。受众可以直接从首页感受到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差异。所有图片均为黑白照片,呈现出“历史文献” 这一定位: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的地位和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平等的民族政策下,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
从内容上看,大多数照片描述了少数民族的具有陌生感的生活方式。图片往往记录正在发生的活动,生活场景和仪式节庆等动态鲜活的生活状态。绝大多数图片视觉中心为人物,景别采取中景或全景,同时呈现主体和背景,也强调了画框内的人物关系。绝大多数图片呈现的是多人关系,面部表情自然放松,笑逐颜开。从大量的历史照片中筛选出的这些图片,如何选择和如何呈现,显然是精心考虑的结果。这些照片多用自然的空间呈现,使用抓拍的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画面的真实感和传播效果。
从图片表现的内容来观察,编辑仔细地用不同民族的生活图片搭建了类似民族志式的分类结构。例如,表现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哈萨克族的叼羊比赛、达斡尔族的养育习俗、乌孜别克族的家庭聚餐、阿昌族的窝罗节等具有符号性特征的民俗活动共 12 张;反映各民族人民适应自然环境、进行经济生产和生计活动的图片17张,如蒙古族青年在草原上放羊、侗族孩子在放学后抓鱼、纳西族姑娘在捻线、撒拉族妇女从事灌溉、普米族人在泸沽湖织网打鱼、珞巴族人的收割、基洛族妇女织布,等等;也有不少图片集中于民族服饰和面部特征(11张),如抱孩子的藏族妇女呈现了正侧面的藏族妇女服饰和头饰(1950年)、在路边洗脚的彝族学生(1980年)呈现了彝族少女的服饰和优雅体态、瑶族妇女(1981年)的图片则把重点放在特别的帽子和上装上、塔吉克族妇女和女儿(1985年)同样呈现了自然美景下的服饰细节;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着重于歌舞表演(6张)、民间艺术(6张)的图片。另外,独龙族的人们走过吊索桥(1985年)强调了生存环境和勇气,拉祜族学生在田间做化学实验(1978 年)、德昂族学生在田间听课(1976 年)则凸显了少数民族努力走向现代化的情景,关于汉族的图片拍摄的是退休后的老人在鸟笼环绕的房间中写一本关于鸟类的书稿(1963年)。
从人物角色来观察,女性和孩子形象成为该专题着重强调的内容,除去群体场景之外,其中32张图片的主体人物为女性,除了强调性别地位平等的理念之外,这与女性民族服饰更为传统、变迁较少的原因有关——几乎所有的图片都需要交代民族服饰。因此,女性既出现在民俗活动的现场,也在劳动的场景中点缀画面。以孩子为主的图片 14 张,呈现童年的天真、学习的激情、成长的快乐等内容。以成年男性为主的图片为5张,呈现头人的威严、节日的愉悦、竞技的勇气、家庭的和谐的意向。
其中,《1964年的傈僳族孩子》关注了一群傈僳族孩子的民族服饰和灿烂笑容,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都身着传统的傈僳族服饰,在向画面左边看去的同时露出了欢乐的笑容。画面稍远的后景处,一些男性青年穿着中山装,带着军帽,显示出具有时代感的主流打扮。图片应该是在集体照的现场抓拍,充满画面的笑脸传达了欢乐祥和与积极向上的情绪。该图的图片说明则致力于客观描述傈僳族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征:“居住云南的傈僳族人民热情开放,善良诚实。他们的主食是玉米和荞麦。某种药草(Gall)被认为具有药用质量,用来清洁肝脏和消化道,还可以做成调味品。它常与葡萄酒或煮熟的肉混合在一起,通常他们会先将食物传给老年人,表现出他们的尊重。”①如果用它和早期传教士和探险者拍摄的傈僳族图片进行对比,我们就会马上发现,后者的傈僳族形象,是在明显的权力差序中僵硬、拘谨、怀疑、紧张、不耐烦或气愤的情绪的“他者化”形象。②
在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四个县设立了工作委员会,随后解放军进驻傈僳族分布区,傈僳族终于获得了解放。在解放初期,傈僳族还是保持着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些元素。这张拍摄于 1964 年的照片呈现了傈僳族作为国家建设者形象的巨变。画面中的傈僳族孩子天真和自发的笑容具有很强感染力,他们自信的精神和体态也令人注目,成为傈僳族社会发展和地位变迁的历史证据。专题中傈僳族图片的选择,让我们也感受到了作为国际传播的视觉“前台”,欢笑的傈僳族孩子们的集会照片,背后似乎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粗暴观看下的一种反向建构和无言反抗。——论文作者:熊 迅
相关期刊推荐:《民族艺术》(季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刊物。刊发各类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