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1-07-0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155次
摘 要: [摘要]西方学界对历史想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启蒙时期,康德的演绎逻辑和维柯的诗性智慧提供了对想象的两种不同理解,并影响了此后的历史想象观念。随着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大部分职业史家视想象为历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随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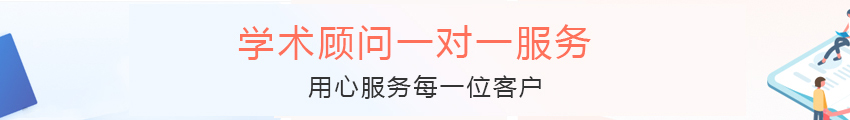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西方学界对历史想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启蒙时期,康德的演绎逻辑和维柯的诗性智慧提供了对想象的两种不同理解,并影响了此后的历史想象观念。随着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大部分职业史家视想象为历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随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怀特分别在认知和话语层面为历史想象进行了辩护。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无法剔除想象,历史想象在其中发挥着连接、综合或预构史料的作用。历史想象对史家探寻历史过程,理解历史意义不可或缺。有关历史想象的探讨启发我们思考一种不只包含了事实,还可能蕴含着伦理和审美维度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历史想象;历史真实;柯林武德;海登·怀特;历史认知;历史话语
“想象(imagi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imāginātiōnem”。其与名词imāgō相关,imāgō有“模仿、复制、再现”的意思,在修辞学上特指“比较”,在艺术领域意为“描写、表达”。从imāgō可衍生出动词imāginor,意为“构思、设想”。因此,“想象(imaginaion)”最初有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构想、摹仿、再现和描绘之意。在汉语中,“想象”一词为动宾结构。《说文·心部》:“想,冀思也。”《说文·象部》:“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①《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②可见,在中文里,“想象”也有依据客观事物在头脑中进行构想之意,它与英文imagination的最初含义有暗合之处。在现代哲学解释中,“想象”通常被视为一种思维能力。如《哲学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一种在心灵中构造图像或其它不是直接源自于感官之概念的能力③。张世英指出,“想象”基本意指“飞离在场”,即一种“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能力”或“经验”④。通过想象,我们能够回忆过去的事物,或构建出一个被认知了的场景,虽然这个场景可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对应物。所以,大家通常不会否认,想象是文学和艺术家必备的一种工具。借助想象,他们能够超越现实生活,进行“虚构”的工作。
但想象是否是史家必需的思维工具,却是一个争论中的议题。一方面,历史学的要义在于求真,这要求史家严格依据史料,对过往的经验事实进行仔细地调查研究,以确保其叙述最大限度地与事实相符。从这一层面看,历史学排斥想象。但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家无法再感知和知觉的过去事件,史家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对之进行经验观察,或用卡西尔(ErnstCassirer)的话说,无法“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⑤。因此,就使过去不在场的事物再次显现而言,想象对历史学又至关重要。关于想象在史家头脑中发挥的作用问题,张耕华、杜维运、李剑鸣等国内学者都曾作出论述。他们肯定了想象是史家所能使用的一种思维工具,但同时又认为史家在使用这种思维工具时要“适度”“平衡”“辅助”性地运用,以确保历史的真实①。这样的说法得到学界的大体认同,但也留有很多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如果说想象确实是史家的一种思维工具,那它是必需的吗?假设史家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证据,那么他还需要想象吗?想象的参与是否意味着背离实在?本文试图围绕着这些问题,回顾和考察西方史学思想中不同学者针对历史想象的思考,总结、比较其中的共识和差异,以期引发学界对历史想象问题的重视。
一想象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位置
按照“想象”一词的词源,其有以客观事物为原本进行复制、描绘的意思。据此,柏拉图哲学将想象置于认识过程四阶段(想象→信念→理智→理性)的最低位置。在柏拉图看来,人类认识的最高任务在于追溯感性中直接在场的东西的原本,即永恒在场的“理念”;而想象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它需要借助回忆,其所得产物归根结底是一种虚幻,并非纯粹在场②。这里,柏拉图考察的多为绘画和诗歌中的想象,他轻视这类工作在认知中的作用。虽然柏拉图没有说明历史研究中是否有想象成分,但他也不看重历史,因为历史研究变动不居的事物,它所产生的不过是一种“意见”,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真知”。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将想象性的诗歌与历史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旨在提供审美体验和普遍的道德教益,后者旨在提供行为指导和进行探究活动③。亚里士多德把历史置于比诗歌更低的位置,因为历史描述的仅仅是一些“流水账”,而诗歌多少揭示了人类本性及人类行动中的普遍意义④。即便如此,想象性的诗歌仍然比追求永恒和理性的哲学的地位低。因此,在希腊哲学中,怀疑、抑制想象的观念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情况到启蒙时代方有所改变,伴随着思想家对想象的深入思考。
启蒙时代对想象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分别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和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Vico)为代表。康德把想象视为人类知识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他区分出两种想象:一为“再生性的想象力”,指一种回忆或联想,它“只是服从经验性的规律即联想律的”,因此没有脱离柏拉图的窠臼,“对于解释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毫无贡献”⑤;“创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Ein-bildungskraft)则不同,它是一种“先验的想象力”,是前者产生的基础。康德将人类认识分为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两个层次。通过感性直观,我们接受物自体刺激而所产生的表象。借由感性直观中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将杂乱无章的表象在感性中综合起来。在感性直观之上,四组十二对的先验范畴又构成一张认知之网,把分散且无联系的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先验想象力就起到了沟通直观和范畴、感性与知性这两种本质上异质的认识能力的作用。因而,想象力同时具备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的特征。一方面,它能够把杂多的表象带到综合中,另一方面,它又能通过时间规定与知性范畴契合,从而把同一性带到综合中⑥。
具体来说,先验想象力发挥着两种作用:其一,它能够把在时间中先后呈现的各种感觉因素结合为单一整体的感觉对象。例如,能够把一条线的第一段、第二段等等与最后一段综合为一条整体的线;能够把第一天中午到另一天中午的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缘于先验想象力的这种作用,已不在场的先行表象(直线的前一部分、时间的先前部分)得以在思维中再生出来,并且与继起的表象综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二,想象力可以通过“图式”(Schematismus)把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结合为经验知识。例如,当我看到面前的一本书时,通过图式,即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作用(或者说,形象综合),我得以把感觉中直观到的东西和“书”这个概念综合为一个单一的经验———看到一本书的经验,这是一个将知性概念加以直观化、感性化和图形化的过程①。根据这些作用,想象力就在康德论证的演绎逻辑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它是人类一种理性的先验能力,在知性建构人类科学知识大厦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和创造者的角色。同时,在演绎逻辑中,知性概念和经验材料又规定着想象力:前者赋予想象力以必然性,把它综合在一个系统中,不致让其成为一种天马行空的、盲目的东西;后者又赋予想象力以实在性的基础,不致让其成为一种虚幻的空想。
维柯则在不同层面理解想象。康德的观念部分来自于笛卡尔,笛卡尔又追随柏拉图,认为只有先天的观念是确定的,因此,所有基于感性经验的知识都无法提供绝对的确定性,历史学即属此列。维柯则是彻底的反笛卡尔者。他认为,由于人创造了历史或人类世界,因此人能够认识历史或人类世界;类似的,由于自然界由上帝创造,因此只有上帝能够认识自然界,人无从认识。这样,历史这种在柏拉图和笛卡尔那里无法获得确定性的“意见”便被抬升到知识的地位。
想象在维柯所谓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柯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方法和眼光,且皆合理。其中,在原始阶段,人们(如荷马)借由活跃的想象,“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形成“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genera),从而“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纳到这种范例上去”,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同时,由于个体和范例间的相似性,借由想象所得到的“想象的类型”必须被创造得恰如其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想象类型也可以被视作真实的②。由于想象是人类思维模式的最初阶段,伴随着人类阶段的成长,在想象之中便诞生了理性。“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苏格拉底)才用归纳来引进辩证法。”③这样,依照原本进行的想象的比喻就成为理性的辩证法的“前身”。通过这种方式,维柯就把被柏拉图、笛卡尔贬低的想象提升到与逻辑同等的位置上。如果说逻辑作为理解的一种方式,它是抽象的,是对概念的推演,那么想象作为理解的另一种方式,它就是具体的,是对意象的运用。
康德和维柯对想象的理解在之后对学者们认识历史想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想象便是这两种想象杂糅的产物。在有关历史想象的早期论述中,接受了康德和赫德尔(JohannGottfriedHerder,他在德国发现了维柯学说的价值)观念的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认为,历史认识不仅要观察到孤立的、零碎的外部事实,更要凭借感觉、猜测去把握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和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创造性认识———理念(eineIdee),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方可称为真实的。要把握内在因果联系和理念,就必须运用想象。在这里,想象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直觉能力(intuitivefaculty)或关联能力(connectiveability)。通过它,史家可以填充和联结他所直接观察到的杂乱无章的片段,找到个体事件之间的必然性,从而达成历史真实。同时,历史真实本身是多样的,富于个性的,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模式④。这便与康德式想象所达成的普遍知识区分开来,更加强调历史想象的特殊性。此外,洪堡也承认史家所用的想象与诗性想象的共同之处,但他仍然区分了二者,认为不同于诗人,史家必须要将想象置于对实在的经验和观察之上。洪堡的这种历史想象观念不是孤立的,到20世纪初期,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观点的相似物。
二对历史认知中想象的论证
洪堡生活的年代恰是西方历史学经历专业化变革的时期。随着历史学成为大学中一门固定的专业科目,它逐渐完成从修辞学中脱离出来的过程,确立起自己规范的方法论及教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与此同时,文学(literature)和语文学(philology)逐渐取代古典时期的演说和修辞学,成为有关写作和语言的一般学科。历史学同文学、语言学在学科设置上有了清晰的界限。这条界限在思维中的反映,即要求史家告别用想象来构想真实事件这种前现代的行为,以便能够把史学同神话传说(这被认为是文学的研究领域)区分开来。因而,一些促成和接受专业化的史家有意识地试图抑制想象。兰克(LeopoldvonRanke)曾清晰地表达过这种看法。在其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导言中,兰克写道:“书的写作形式取决于其目的和主题。因此,历史著作的写作,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文辞华美、想象丰富,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则。”①这里,兰克实际上将想象设想为在修辞上起作用的事物,它会“拖累”历史事实,因此要在“著作里避免一切创造和想象”②,史家只需如实直书。
相关期刊推荐:《史学月刊》是河南省历史学会和河南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历史学专业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本刊主要栏目: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评论、专题研究、社会史研究、城市史研究、乡村史研究、电脑与史学应用、生态环境史研究。
即使是文风华丽的浪漫派史家麦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他一方面重视人的情感,认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另一方面又补充说:“(史家)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历史学始于小说而终于散文。”③在麦考莱看来,历史学的肇始得益于其与虚构作品间的暧昧关系,但历史学的发展使其脱离虚构作品,成为描述过去的真实文本。麦考莱实际上同兰克一样,认为想象在“文体”(style)层面发挥着作用,它与历史认识无关,属于次要的语言装饰,仅使得历史呈现更为生动。客观主义者兰克较麦考莱极端之处在于,他认为即使是这些文体中的修辞因素也要一并去除。
兰克和麦考莱的观点代表了实践史家所推崇、遵循的一种规范:史学的求真意味着史家要凭借科学方法,尽量捕捉一切琐碎的事物,发现过去“尚未讲述的故事”,谨防想象在修辞上添枝加叶,从而使历史记述能够与过去实在相符合。这一规范暗示着史家头脑中潜存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历史实在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等待着被发现,而事实之间的联系已然存在。实际上,史学家的思维工作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假定起着文体式功能的想象能够被排除出去(事实上这不可能),发挥着康德式认知作用的想象也无法被排除。20世纪初,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的史学家艾伯特·哈特(AlbertBushnellHart)在一篇专门论述历史想象的文章中写道,想象是一种“心灵的高级能力”,一种“高尚……的能力”,一种“心灵的神秘力量”,想象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像是把事实的枯骨装配起来使它们复活④。哈特的这种观点与洪堡的有些类似,但他浪漫化的论述并没有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在哈特作出上述论述的十多年后,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更为系统、也更为有力地论述了历史想象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柯林武德认为,史学家的工作遵循这样一个程序:他需要依据某一标准对史料及其中的论断进行批判、选择,获得诸多点状的事实,然后在事实间进行推论,获得众多线索,最终得到一幅自我融贯的整体图画⑤。在这一程序中,想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历史推论的过程需要想象的参与。史学家需要利用想象,在固定的事实、即单一论断之间插入史料所不曾提及的东西。例如,史学家从证据中得知,凯撒第一天在罗马,第二天在高卢,那么,他就要借由想象把凯撒从罗马到高卢的行程连接为一个连续的整体①。在此,历史想象相当于一种理性推论,它发挥着综合式的建构功能,将点状的事实串连成线,构成一个整体。其二,对史料及其中论断进行批判、选择的过程也需要想象的参与。对史家来说,事实的点并非固定,需要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他要对原始材料反复加以检验、驳斥,以确保所构成的整体图画融贯而没有冲突。而史家借以批判的标准,正是由历史想象构成的整体图画提供的,这幅整体图画对事实发挥着引导功能。柯林武德指出,这个整体的网“乃是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远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它实际上是充当了我们用以决定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②。由此,在柯林武德这里,历史想象不再是麦考莱式的装饰性的想象,而是一种认知的想象,他称之为“先验的想象力”(apriopriimagination)③。
那么,柯林武德先验的历史想象力与康德先验的想象力有何联系呢?柯林武德认为,首先,这种先验的历史想象力同样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人类心灵普遍和必然的方面,是“任何史学家在拥有这些证据时都会想象的,在任何情况任何氛围中思考相同的证据时都会想象的”④。其次,如同康德的想象力能够让我们“看见”超出实际感官感知的客体,如月亮的背面、未破壳鸡蛋的里面;先验的历史想象力能够综合连接起众多事件,将之构成为一幅整体的、融贯的历史图画。但历史想象又稍不同于认知想象,它“以想象过去为其特殊的任务”⑤。历史想象归根结底是对特殊事物、对个体的认知,其最终实现的不是康德知觉想象所得到的普遍的、科学的类(types)。此外,历史想象针对的是史家无法经验的、一去不复返的事物,“那不是一种可能的知觉的对象(因为它现在并不存在)”⑥。
然而,如果是对特殊事物、对个体的认知,这种想象力就与文学艺术家的想象力有些相似,因为文学艺术家正是要凭借想象力描述出不同个体及其个性,进而构造出一幅融贯的整体图画。柯林武德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尽力区分出两者。他认为,不同于小说家,史学家的图画必须力求真实。首先,史学家的图画需要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其次,这幅图画需要与它自己相一致;因为只有一个历史世界,而且其中每一个事件都必定和其他每一个事件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再次,这幅图画还必须与证据处于特殊的关系之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证据可以是史家认为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但史家的陈述必须要有证据加以证明⑦。由此,通过与知觉想象和文学想象相区分,历史想象的特征便显现出来。
柯林武德对历史想象作为史家先天能力的论述破除了大部分实践史家认为史料是判定历史真实性标准的经验主义观点。现在,一切历史事实都将由史家的主体观念所确定,而非由外部世界所给定。换句话说,只有在观念中,历史事实才能被认识。但存在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仍然是客观的,因为恰恰只有存在于观念中,它才能被理解。“对历史学家来说,他所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并不是要加以观看的景象,而是要通过他自己的心灵去生活的那些经验;它们是客观的,或者说是为他所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观的,或者说也是他自己的活动。”⑧通过这一证明,柯林武德确定了先天的历史想象是史家在观念中客观地把握事实的必要装备。鉴于柯林武德是从理解史料、认知史料的研究过程来探究历史想象的,因此,借鉴当代学者杜森(JanVanderDussen)的说法⑨,我们可以把柯林武德的这种证明视作为历史知识建构的“底层基础”。历史想象是“底层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假如没有了历史想象,史家得到的将是一堆没有经过批判的史料堆积物。——论文作者:金嵌雯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