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27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社会关系内蕴于马克思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的逻辑理路中,其历史性确证了厘清共同体问题的唯物史观视域。马克思从物质利益问题出发,探讨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现实分裂,从而揭开了虚幻共同体的历史暂时性,指明真正共同体蕴藏的利益融合的现实意义;
[摘要]社会关系内蕴于马克思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的逻辑理路中,其历史性确证了厘清共同体问题的唯物史观视域。马克思从物质利益问题出发,探讨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现实分裂,从而揭开了虚幻共同体的历史暂时性,指明真正共同体蕴藏的利益融合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探究物的关系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以辨析虚幻共同体本质,主张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基础重建社会所有制,以这种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成为个体发展的条件;共同体的发展还内蕴着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交往关系的历史嬗变,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由制约转向依存,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由工具性走向共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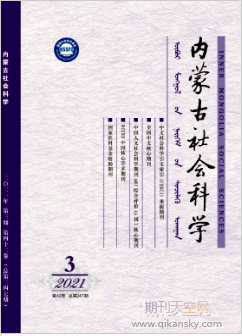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利益关系;生产关系;交往关系
作为马克思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范畴,共同体蕴含着马克思对个体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怀和未来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构想。长期以来,提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有学者从人的生存状态与共同体的关系视角探究共同体发展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1],有学者从“劳动实践”视角阐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生存基础[2],有学者从“共同活动方式”视角探究真正共同体的实践前提[3],这些思路和方法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共同体由“虚幻”到“真实”的逻辑建构已然是学界的共识,这一过程蕴含了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内在弊病的深刻批判和对真正共同体实现可能的阐释。如何能更具体明晰这一自然历史过程,从何种视角说明才能更符合马克思的观点,这些问题亟待从学理上辨明。
纵观马克思的文本,社会关系是马克思思考和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存在物的规定性都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显示出来的,社会关系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是人们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随着生产和需要的发展形成的各种关系。现实生活中,个人为了满足需求总是以特定方式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而后构成共同体。共同体成为由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形式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体。因而,共同体是一个关系存在,共同体内部的各类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日益复杂化。
因此,尝试从共同体的横断方面剖析共同体的内在结构,认识各类社会关系的内在要素和相互作用,理顺各类关系生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助于打通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的现实路径。其中,特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和主体间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视角考察共同体的具体方面。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共同体展现不同的样态,其内蕴的利益关系、生产关系和主体间交往关系有其特定的内容。这种基于过程性思维和社会关系视角思考共同体的方式也为我们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参照和现实进路。
一、利益关系由分裂走向和解
在马克思的研究视域中,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初表现形式,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普通的关系,它所具备的时空条件性为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冲突和融解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借由对莱茵报工作时期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入考察,发现了隐藏在各种“物”背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在这种客观关系视角下,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由于分工引发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裂越发明显,虚幻的共同体随之生成并最终成为特定阶级利益关系的承载体,由此引发的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其最终走向消解。可以看出,真正的共同体内蕴的利益关系和解的应然状态并不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而是在对市民社会现有利益关系的实然状态以及发展走向的科学考察和理性批判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展现了马克思阐发共同体问题的独特思维方法。
(一)利益是共同体关系的基石
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为马克思从客观关系视角探讨共同体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刚踏入实际工作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就以捡枯树枝为例,马克思认为,枯树枝是树木这一财产的附属品,贫苦人民捡枯树枝是对已脱离树木本体的附属物的合法占有,而盗窃林木是对树木所有者财产即树木本身的私自占有的违法行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然而,特权阶级掌控国家立法权并制定了林木盗窃法,抹杀捡枯树枝与盗窃林木的差异,将捡拾枯树枝的行为判定为非法行为,以法为媒介强化特权阶级利益的优先性,同时弱化贫苦阶级基本权利的合法性。这种以私人利益为参照系制定国家法律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对于“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命题的理解。国家理性与私人利益的逻辑断裂,促使他反思共同体的合理性以及物质利益的地位问题。
随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入探索,马克思对于国家和法等共同体本质的认识从抽象意志转向现实的物质利益基础,并看到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关系的决定作用。这种客观关系同各阶级的物质利益紧密相关,影响着财产所有者尤其是政策决定者的观念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和法律的具体运行。利益成为共同体关系的基石。马克思在考察摩泽尔河沿岸居民状况时指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4](P.363)。换而言之,社会等级的观念与行动往往遮蔽了一种“关系的客观本性”,国家和法等共同体受到各等级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支配和制约。因而,贫苦阶级所遭遇的问题不是一种突发的简单状况,而是社会管理阶层与贫苦阶层的物质利益冲突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不合理的关系,从制度上改变腐朽关系。至此,马克思业已开始转变囿于理性立场而空谈社会现实问题的倾向,并致力于从各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中探究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和解决路径。因而,利益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成为影响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共同体样态的关键因素。
(二)批判虚幻共同体的利益分裂
真正共同体利益关系的建构并不是一种道德预设,而是建立在对虚幻共同体内部利益分裂的实践批判基础之上。马克思把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置于现实关系之中进行研究,认为那种以“普遍性的形式”追求特殊利益的现象正是虚幻共同体的现实表现。利益以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是一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利益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出多样的外化形态。伴随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产生了特殊利益以及由交往而联合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5](P.536)也就是说,国家作为超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第三方力量,是社会多元利益集体分化后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是共同体借以化解利益矛盾的工具。可见,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存在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协调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是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实现阶级统治的合法化。
然而,虚幻的共同体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5](P.537),它不代表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仅仅是共同利益在形式上的独立形式的虚幻载体,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就现实而言,统治阶级要确证自己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就要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达为适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促使社会成员在追求所谓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去实现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5](P.552)。因而,原本为了协调利益矛盾的共同体变成了个体发展的桎梏。资本条件下的特定经济结构引发了阶级对抗,“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成为“非此即彼”的不相容关系,阶级的自由和压迫、幸福与痛苦成为相对立的存在。就这样,统治阶级作为特殊群体的利益越来越扩大化,而真实的共同利益被掩藏在帷幕之下。国家和法因其不再是共同利益的现实存在形式,而是仅仅作为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而异化为虚幻的共同体。因此,要探究真正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就需要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关系入手,而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实践批判则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三)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的消解
马克思认为,社会利益关系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呈现的对抗性质是虚幻共同体阶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和私有制的伴生物,必将随着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而终结。因而,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矛盾的和解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造成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利益冲突的根源不在思辨中,而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因而,消解利益矛盾就只能通过革命的实践来完成,从根本上否定虚假共同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达到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真实性和高度统一。而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必须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形成,以无产阶级为实践主体,它具有全新的利益特点,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P.42)。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正是符合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在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利益关系的真正共同体阶段,人与人之间处于平等关系,其成员“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5](P.384)。因此,个体的特殊利益不再与共同利益出现分裂状态,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在矛盾中高度统一,共同利益不会阻碍和损害个体利益,个体的特殊利益成为共同利益的有机构成,二者相互保障、相互促进。在这种自由自愿的联合体中,个体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真正达到统一。共同体不再是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设,而是保证每个个体的利益均得到实现。显然,“真正共同体”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是以保障个体正当利益与共同利益高度统一、以清除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抗性矛盾为价值旨归的共同体。
二、生产关系由物化力量向内在力量转向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而且是社会关系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只有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7](P.2)。因而,考察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的历史进程,就要沿着物质利益关系这一客观关系的道路继续深化,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深入到市民社会中考察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人类劳动对象物的抽象物性。这种人与物的关系所发生的目的与手段之关系的颠倒,既不能靠倒退到自然共同体人的依赖关系中去完成,也不能“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依靠物的力量变革物化社会关系和私有制关系,从而构建合理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再是控制和制约个体的外化力量,而是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手段。
(一)从人与物之关系的颠倒解蔽虚幻共同体的物化本质
马克思深入到政治经济领域对虚幻共同体开展研究,深入到生产和流通领域考察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生成和积累过程,从而厘清了人类劳动产品对象的拜物教性质。虚幻共同体内部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抽象的社会关系之“物”替代了所有物的直接物性,劳动者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被物之间的抽象关系所遮蔽。
在商品社会,私人劳动不能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印证自身。因而劳动的价值必然通过外在的物来体现,人与人之间以商品交换的形式产生关系。“人”的意义就是以商品这类“物”来表现,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外在地显现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P.89)货币的产生成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一般等价物,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它“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8](P.93)。继而,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要素的双重规定促使资本行使物化的权利,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强化雇佣劳动制度,进而促进物化关系的生成。因而,作为人类劳动对象物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所蕴含的物的力量原本是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应该是从属于人而存在的,但它们却成为外在于个人并控制人的力量,从而成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个人和共同体则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且,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劳动产品对象的物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反映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表现为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这种物化关系体现了虚幻共同体内在的矛盾裂变,这种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原则对个人而言成为外在的、强制性的外化力量。
马克思进一步从世界历史视域出发,指明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对外开辟的空间载体,不仅没有消解物化社会关系的困境,反而成为物化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媒介。资本在全球范围开发和落户,将自身生产方式的基因序列复制到各民族,同时不断发展着资本自身的否定性因素。它将世界历史空间范围内各民族的封建羁绊清除,却又被置于物化社会关系的控制下。全球范围内分工的不断固定化和精细化促使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的压迫性不断增强。世界市场所创设的空间内蕴物质化社会关系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性特征,从而诱发全球范围内不同阶级之间的反抗和对立。总之,物化社会关系在空间范围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展现了人和物颠倒性关系的强大的可复制性,资本空间扩张引发的危机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为扬弃以“虚幻共同体”为代表的上层建筑和开启新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现实的主体力量。
(二)物化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预示了真正共同体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物的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5](P.542)。而现实的革命就是要实现对使人逐步工具化的物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成为一种逻辑使然。这种逻辑使然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物化生产关系逐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要素,虚幻共同体成为个体存在的桎梏。因此,物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预示了真正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相关期刊推荐:《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于1980年,本刊为双月刊。设有:专论,民族·历史,政治学·法学,哲学·科学,文学·语言,经济·管理,西部论坛,编辑出版学等栏目。其中,民族文化、北方民族历史、蒙古国研究、西部论坛等栏目独具地域特色,在学界相关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这就必然要求变革物化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使其重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而,建构真正的共同体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实现人与物的关系“再颠倒”,实现人们对物的异己经济力量的自觉支配与重新驾驭,使之服从于人与社会自身发展的过程。“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9](P.97),虚幻共同体的物化生产关系的隐秘特性才会被揭开。其次,马克思认为,要辩证认识虚幻共同体的物化属性,既要看到物的力量内部蕴藏的否定性因素,也要认识到物化在特定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基于此才能正确认识消解物的力量的方式。从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到“物的依赖性”阶段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关系日益扩大的产物,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虚幻共同体内部否定性要素的消除也要在自然历史过程中开展,要借助物自身的力量,在高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消除私有制等实践手段来消除物化。卢卡奇也看到了物化对人的侵蚀,看到了无产阶级是消除物化的主体力量,但他却走向了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消除物化途径的道路上。但是,马克思的观点是,“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5](PP.570~571)。摆脱物的控制不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成为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难题。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人类生存方式由虚幻共同体到真实共同体的客观发展进程是不能先验的、不能从某个思想家的理论出发的,而应回归到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和客观性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借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借助社会变革的力量,使人被自身产物支配的现象在历史中自然而然地改变。
(三)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基础重建社会所有制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系统,所有制关系是所有社会生产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方面。因此,变革物化社会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变革所有制关系。物化社会关系的形成根源在于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变得狭隘和片面。因而,“真正的共同体”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P.874)。这种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一种否定,其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所有制。这种社会所有制作为未来共同体的所有制形式,是使生产关系由外在性压迫力量转化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条件的内在力量。换句话说,马克思提出重建社会所有制问题不是现实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而是在对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和个体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的宏观意义上的哲学考量。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通过劳动在外在世界中表征自身,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反映了劳动性质和方式的不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私有制由于自身的不可持续性必然要被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公有制所取代,个人不再被物所支配,生产资料被社会全体人所占有,每个个体以劳动为中介使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0](P.18)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从而彻底实现了劳动解放。当外在的社会条件不再以异己性存在后,劳动从雇佣关系中解脱出来,劳动产品不再具有拜物教性质,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实现了统一,劳动不再是为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成为自身的内在需要。人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生产劳动,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人的规定性。
三、交往关系由二元对立走向和谐共生
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的过程,内蕴着个体和共同体主体间交往关系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共同体由“虚幻”走向“真实”所内蕴的主体间性的思维向度。这种统一关系的建构具体表现在:消除由物化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撕裂,达到自由个性的个体与共同体的依存关系;消解个体间关系的对立,促进个体间的和谐共在。
(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奠基于生产关系
如上可知,马克思把对物化社会关系的分析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从根本上找到了虚幻共同体的内在弊病,从而实现对物化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批判。从物和生产关系等范畴入手,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看到主体间交往关系问题。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生成的物质交往关系,从外延上隶属于交往关系。同时,交往内在于生产活动之中,主体间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实践中生成的。因此,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和交往实践中互相影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交往关系的外化形式。马克思在看清虚幻共同体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从价值视角和人的生存状态看到了主体间交往关系。主体间交往关系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反映了不同历史区间共同体的性质。因此,有必要将人、主体性和价值等范畴自觉地纳入到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中,在探究共同体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关注共同体内部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样态,以寻求交往和生产的良性互动关系。
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马克思考察共同体问题的核心范畴。马克思考察的个体是“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只有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性。现实中的个体是在与其他个体的相互联系中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和社会化的,人自身的所有关系也只有通过对他人或者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得以体现。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蛰居其中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主体间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两类关系在不同形态的共同体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是与其所在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并为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提供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由制约走向依存
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建构共同体理论的中心线索之一。在虚幻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的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性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11]。虚幻共同体的物化社会关系消弭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限制了个人的发展。物的力量将全体社会成员编织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网络之中,并将其变成统治现实生活的唯一的、绝对的关系,使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消失,单一化为抽象的交换关系。马克思深入到日常生活中考察了“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考察了雇佣劳动者被支配和奴役的弱势生活境遇。他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2](P.469)令人吊诡的是,雇佣劳动者为了生存,被迫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他用自己的活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而转化为资本家奴役劳动者的资本。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格,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8](P.10)资本家显然也不是“真正的个人”,而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成为外在于雇佣劳动者的支配力量。不论是资本家还是雇佣劳动者,都没有逃脱物化的力量。共同体中个体的个性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明确的共同体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个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个人”,而是成为受到物化社会关系制约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承载体。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是人格化的活劳动;而资本家则成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是人格化了的资本。
真正共同体是人的自由个性真正展现的历史阶段,它是对人和物在手段和目的关系上的再颠倒,具有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的“真正的个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考察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将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关系作为理解自由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革命走向真正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的主体不再是虚幻共同体的“私人”或者“利己主义的原子个人”,而是“真正的个人”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这种个人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时间不再成为货币单位的价值衡量尺度,而是真正被置于个人的支配之中。马克思认为,“自由个性的个体”与“联合体”两者处于互动和依赖关系中。只有通过联合才能消解由于分散性所引发的剥削性力量,个体重新获得控制自身社会关系的条件,才为全面发展提供潜在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P.571)真正的共同体既是作为自由个性的真正的“个体”,又是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体”,所以是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论文作者:郑冬芳,王静宜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