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4-11-0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301次
摘 要: 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许多受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优秀著作[7]。作为西方学术的重要一环,虽然它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与我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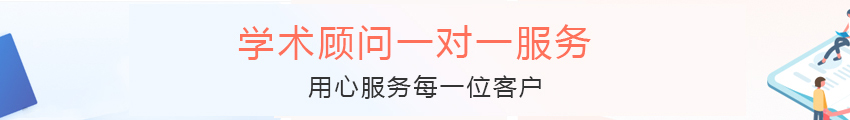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许多受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优秀著作[7]。作为西方学术的重要一环,虽然它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与我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以期为开拓国内历史学视野增添色彩。
一、方法探析
1.区域研究的创新视角。
倡导区域研究,是费正清开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与传统欧洲汉学研究范式所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点。区域研究又称为地域史研究,将研究的范围专门固定于某一特定地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其内在的自然环境、社会阶层、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交通状况、政治制度等。施坚雅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将中国横向分为9个大区,运用区位理论、“中心地”的原则以及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的内部结构与外界联系[1](P60)。王笛的《茶馆》书著,运用区域研究方法,描绘了近代中国大众生活的侧面。王氏将研究视角投放于成都,冀通过对该区茶馆的叙事,窥探当时中国“市民社会”的相关状况。王氏将成都的茶馆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样本范例,对茶馆的社会地位、经济运作以及政治斗争等相关历史面貌做出详实的叙述,生动地刻画出成都市民斑驳陆离的生活百态,且透过微观研究和宏大叙事有机结合,解读了国家政权和组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是如何向下层渗透的大命题。学者在民间文化和大众宗教领域,也倾向于区域研究方式。譬如,万至英曾就民间信仰形象的历史沿革研究时,强调区域视角为切入,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民间文学与信仰、女性地位及财富、家庭观念等多重维度的研究[5](P143-196)。华森亦选取了两个富有代表性村落为案例,通过分析区域内特殊的道义经济体系、地方精英统治、社会分层、祭祀庆典等侧面,披露出“天后”正统化的过程[5](P57-92)。总而言之,区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克服“通史”重广博而轻精深之瑕疵,为研究者提供一条深入解剖历史真相的渠道路径。
论文推荐:《社会工作》(双月刊)创刊于1988年,是江西省民政厅主管、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份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为CN36-1263/D,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672-4828。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际着名社会学家雷洁琼题写刊名,着名专家学者陆学艺、郑杭生、卢谋华、王思斌、王青争、孙士杰等担任学术顾问。创办以来,得到国内社会学界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全国各级民政部门领导和广大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大力支持。被评为江西省首届优秀社科期刊,江西省一级期刊。
2.计量史学的运用。
计量史学是指利用数学和推论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数据统计,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再把定量结果用于历史验证。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为数据分析和信息存储提供便利,计量史学运用于社会史等史学研究领域。计量史学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贡献颇大。施坚雅分析四川农村社会的经济数据,提出了“市场层级理论”[1](P7);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通过定量分析“满铁”调查的数据,提出了“小农经济过密化”理论。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成功之处也得益于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周锡瑞独辟蹊径,以定量和定性区分史料。定性史料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定量史料以及以此为依托的资料库构成了周氏本书分析和写作的基础[2](P6)。周氏创建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内各县的人口数量、县级人口密度、各县士绅力量、自然灾害的频次及各地盗匪案件数量的数据库,他根据特定的公式将这些史料信息换算成量化数字。周锡瑞在具体分析山东地区自然灾害时,统计了各县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及因自然灾害而获免税特权的次数,综合换算出“灾害指数”。另则,根据各项目中独特的运算法则,周氏对山东各县的人口密度、地主所有制程度、士绅力量等也进行了换算,按照相似性原则将程度相近的县城划归到同一地区,是故将山东省划分成六片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区域,这又为他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计量史学可助研究论点及论证更加精确化。计量史学的宗旨就是用“数据”说话,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字语言”所具有的精确性,是传统史学中常用的定性分析难以比拟的,因而能使史学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当然,计量史学也带有其不可规避的局限。有论者指出它受史料的依附程度太深,只有在数据资料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方才有施展的空间,而且数据中的误差和错讹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所以,学者绝不能忽视鉴别史料真伪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科学评估后的数据,方可助益于学者正确探求历史的真相。
3.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尝试。
随着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大举进军历史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孔飞力著《叫魂》书著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相当成功。读者可以发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民俗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痕迹。“盛世”篇章中,孔飞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墨西哥银币的加速流入、中国白银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人口增加压力变缓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介绍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加大,解释外地人增多的复杂经济现象的背后因素[1](P43-50);他借用了社会学中的概念,说明普通民众“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1](P287)的处境;孔飞力亦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在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的汉化、腐败等问题,通过叙述清剿叫魂案“妖首”的政治运动,细致地探讨了不同层级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从乾隆的朱批档案中揣摩乾隆对待下级官员的心理和感受。此外,孔飞力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民间观念对灵魂、鬼的看法和观念进行具体分析。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含,很巧妙地融合在历史的画卷之中。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也吸收了社会学科的成果。此书中的核心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杜赞奇将其指代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官僚化及向基层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为了克服单一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弊端,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杜赞奇藉此分析国家财政收入和政府机构数量增加,但政府职能却未有相应增强的根源。杜赞奇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3](中文版序P2),他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了政治博弈。
二、研究特色
以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及多学科交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色。首先,微观史学异军突起,以小见大的描述成为史家叙述历史的新途径。在区域研究的指引下,研究者可以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甚至集中到某一事件的发生发展、某一人物的命运或者某一个场所的变迁层面。王笛的《茶馆》将成都的茶馆当作解读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一个文本,通过解读茶馆作为一个日常的休闲场所、一个经济实体以及政治角色所具有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描绘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而且也展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机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间的冲突和妥协。其次,将叙事与分析有机结合,并且突出文化在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是,社会文化史的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告诉读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将叙事和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读者解释历史事件背后文化的作用。《叫魂》凭借其流畅的文笔和生动的情节被公认为叙事史的佳作,孔飞力先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就是边叙事边分析的。例如,在描述了妖术大恐慌的兴起和蔓延之后,孔飞力先生通过解读清代的碑刻和小说来了解民众心中的鬼神观念,从而分析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又如在描述完全国大清剿的失败和叫魂闹剧的草草收场,孔飞力又从制度层面对官僚君主制中的非常规权力的运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揭示出在这个事件中君主、各级官僚和下层民众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这种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特点在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周锡瑞在讲述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具体过程时,也总是细致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民间文化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考察这些群众运动是否与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仪式。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锡瑞先生对文化因素的重视。第三,突破西方中心观,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求社会发展的力量。费正清开创的现代中国研究是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导向,这种研究取向须有“假定预设”,即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这种模式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后来的史家逐渐察觉其弊端,并在新的社会文化史中加以修正,将探寻历史发展动因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的本位社会。例如,周锡瑞虽然指出西方的经济渗透给山东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造成了冲击,而且洋教的肆虐也是直接造成教民反抗的原因,但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和壮大根本还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寻找原因,一方面它跟清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剿抚不定的态度有关,清廷不明朗的放任态度实际上促使了拳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山东的地方文化,正是山东习武传统中的“刀枪不入”的招式和民间戏曲小说中“降神附体”的仪式,使得义和团运动便于传播,因而迅速蔓延。是故,周锡瑞认为推动是次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