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发布时间:2022-02-17所属分类:计算机职称论文浏览:1807次
摘 要: 【内容摘要】 在媒介技术变革的语境下,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趋势。通过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市郊乡村居民的深度访谈,发现信息传播技术( ICTs) 的可供性,以及乡村人口对技术所提供机会和潜力的感知、采纳,改变了乡村的交往格局,塑造了数字技术时代的乡村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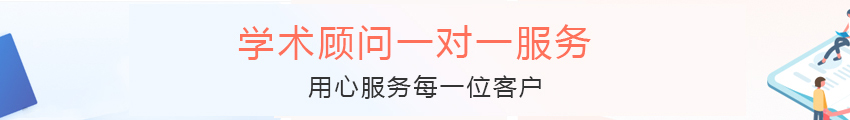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内容摘要】 在媒介技术变革的语境下,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趋势。通过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市郊乡村居民的深度访谈,发现信息传播技术( ICTs) 的可供性,以及乡村人口对技术所提供机会和潜力的感知、采纳,改变了乡村的交往格局,塑造了数字技术时代的乡村社会关系,重现并延伸了在城市化浪潮中遗失的“部落体验”,进而推动了中国乡村“重新部落化”的进程。“部落化”的乡村正成为一个融合现实与虚拟两种向度的文化空间,但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是否会重蹈城市的“覆辙”,在技术中介的离身性交往中逐渐转向“陌生人社会”,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 信息传播技术; 乡村; 重新部落化; 部落场景; 社会关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国,乡村的转型与变迁是各界关切的话题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在谋生压力严峻、空间距离区隔和传播媒介缺席的情况下,他们与家乡的联系、和同乡的交往大幅度减少,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城市的扩张也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离开故土、搬入楼房,原有的社会网络面临破碎重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乡村千百年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受到冲击,“乡村消失了”“乡愁不在了”成为人们的普遍担忧,“重建乡村”的希冀日渐强烈。
但近几年来,信息传播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的普及,既为进城务工人员与远方家乡的亲朋建立即时联系、开展跨越时空的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那些住进“新村”的市郊乡村居民重组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借助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和音视频等多模态符号进行自我表达,亦能在线上建立和亲朋、同乡交往的空间,卷入同步的时空场景中,维系并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在云端实现“重建乡村”的愿景,守护家乡的文化记忆。
信息传播技术为我们寻觅“失落的乡村”带来希望之光,亦有望重构乡村社会的发展格局,传承乡村的文化传统,重塑乡村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被激发、被释放,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颠覆、重构,多元主体在动态博弈平衡中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乡村逐渐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① 作为重新部落化的一个关键之维,乡村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既受到信息传播技术的深刻形塑,也深受主体技术采纳与使用的影响。那么,信息传播技术与主体对技术的感知和采纳如何作用于重新部落化趋势? 媒介技术的变革如何为离乡者提供“重归部落”和“守护乡愁”的机会? 本文希望通过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探索信息传播技术与乡村人口对技术的采纳如何推动乡村重新部落化进程,反思“部落化”的乡村在技术中介的离身性交往中如何维系情感、是否会重蹈城市的“覆辙”而转向“陌生人社会”等议题。
二、相关文献梳理
近些年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在乡村社会的“下沉”,改变了乡村以往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并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以乡村人际关系为主线的社会交往格局变迁,正是考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线索。
( 一) 信息传播技术与乡村交往方式的变迁
作为一种变革性的力量,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空间和地点对乡村人际交往行为的制约机制。村民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对象日渐突破血缘、地缘关系的边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维持社会关系所需要的寒暄、闲聊和娱乐活动将不再强制要求身体的物理在场,基于社交媒体的云端互动使乡村的交往实践转向数字化和“超地域化”。以乡村年轻人的网络游戏实践为例,他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不论是“连麦”互动还是在现实中“靠”在一起,都能通过这种“组团”与“互相帮助” 的模式,增进朋友之间的团结和信任,透过网络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在和参与氛围。②
在公共交往和社会组织的层面,由于我国乡村正处于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村转型的过渡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公共性危机③ ,实体的公共空间日渐衰落。但微信和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勾连了乡村关系。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村民跨越时空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介入乡村公共舆论、传承乡村传统习俗④ ,这为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乡村共同体的再造提供了新的可能。
对于离开家乡的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信息传播媒介也改变了他们和家乡亲友以及其他离乡伙伴之间的互动方式,同时影响着他们建构社会关系和谋求城市融入的策略选择。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纳、使用与城市移民创建和管理自己的社会网络密切相关,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多重身份认同。⑤ 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和革命性扩张,为新生代农民工搭建了一个理想的虚拟交流空间,使其有机会建构起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城市生存与自我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⑥ 除了参与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新媒介技术也实现了离乡者和家乡的重新勾连,保持了和远方家乡的连接,从而参与到乡 村 社 会 的“部 落 体 验” 之中。
( 二) “重新部落化”概念及其分析维度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对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演化的关系作出深刻论断。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作为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化和延伸,其瞬息万里的速度抹除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塑造了即时交互、相互作用的领域,个体知觉与公共经验之间的差别得到弥合,人类的感官平衡重新恢复,任何人都有卷入全球舞台的机会,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⑦ ,人类由此进入“重新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 的时代。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媒介将通过聚合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并让我们保持“电子式地”( electrically) 卷入他人的生活,以将人类重新部落化。⑧ 重新部落化被认为是一个通过“电子手段”重新唤醒神经系统的过程,通过电子媒介实现紧密、实时和同步的参与。⑨
既然重新部落化的出现与技术媒介的革新有显豁关联,那么媒介进化的理论也能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线索。保罗·莱文森曾提出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模型,他认为技术媒介进化的趋势是重现和延伸前技术情境下的传播环境,以重拾在以往的技术延伸中遗失的人性化要素,修复对现实的扭曲和失真。⑩
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观点启示我们,重新部落化并非意味着让人们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乡间村寨,而是 “部落体验”在媒介技术变革驱动下的重现与延伸,是人类的感知系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结构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催化下,以某种征服时空的方式被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媒介的技术制式重新组合了部落成员生活和交往的时空场景,即“部落场景”,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往被区隔的人们将重新卷入时空同步的、去中心化的交往场景之中,彼此共享信息、经验和感觉,其实质是“部落体验”在崭新技术条件下的重现与延伸。因此本文认为, “部落场景”和“社会关系”是研究重新部落化问题时必须关注的两个层面。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从“部落场景”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切入,采用质化的深度访谈法,通过对话和观察来考察乡村人口基于信息传播技术的交往行为和关系实践,以及他们对新媒介技术可供力的感知、采纳和体验,从中管窥乡村社会重新部落化的形成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考虑到重新部落化可能同时发生在不同的乡村情境之中,本文从两类不同的乡村情境入手。
一是以进城务工人员与其家乡亲友的交往和互动为线索,重点关注因时空条件变化、传播媒介缺席而被区隔的离乡者与留守者之间如何实现重新连接。访谈工作在河南省郑州市展开。郑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和工业重镇,汇聚了来自省内乡镇和全国其它地区的务工人员。2020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底,研究者分别在郑州的西部和东部地区选取 15 名在农贸市场、社区和餐饮场所工作的务工人员作为访谈对象,受访者信息见表 2( 编号为 A01 ~ A15) 。
二是以城市近郊乡村为田野考察地点,重点关注市郊乡村被纳入城市体系之后面临的困境和信息传播技术所具有的改变这些困境的潜力。本研究选取郑州市西郊的冉屯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场所。冉屯新村是原冉屯村拆迁后新建的安置社区,居民以原冉屯村民为主,也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和租户,村庄常住人口的构成及特征在市郊村庄中有一定的代表性。2020 年 8 月,研究者通过入户调研的方式访谈了 15 位居民,详情见表 1( 编号为 B01 ~ B15) 。
四、重建部落场景: 信息传播技术与乡村交往时空的重组
任何形式的传播实践都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之中,媒介与传播技术的进化也倾向于重新“书写”时间序列和空间结构,重塑我们对于时空的感知和体验。本部分将结合访谈文本,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勾勒信息传播技术重建乡村部落场景的逻辑。
( 一) 交互的时刻: “集体时间”的重现与回归
在近现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信息传播媒介的采纳与扩散同国家权力关系密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媒介的宣传用途及其所有制结构方面。作为集体所有制的结果,村民对媒介和技术装置的使用行为通常是集体化而非个人化的。这种集体化的媒介接触以及同时伴生的种种交谈、互动,往往是乡村记忆和乡村社会部落体验中的重要元素,媒介使用的“集体时间”也成为人们对故乡的追忆和“乡愁”的构成部分:
受访者 A13: “大喇叭( 指广播) 和电影对我们的集体生活还是蛮重要的。当年经常和隔壁的聚在大喇叭下嗑嗑瓜子,边听边聊,说说这户那户的趣事儿。”
受访者 B14: “在我小时候,感觉大家都特别亲近,说白了就是人都挺好嘞。和同村的朋友买点吃的,等着人家放电影、唱戏,很怀念那种感觉。”
当被问及现在是否经常去电影院观影时,B14 表示: “片子的质量虽然上来了,种类也更多,但那种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感觉就没有了,都是和陌生人坐一起,所以我不经常去。”
“集体时间”涉及部落化情景下家人、亲友、邻里和同乡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其他部落集体活动( 文化活动、传统仪式等) 的时间,反映的是一种集体化的 “信息处理”和交往实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居民每个人的时间结构从总体上看并无显著差别,“集体时间”也占据一定比例。到城市化飞速发展时期,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他们的时间结构和序列趋向割裂、分离,用于互动和集体交往的“集体时间”减少,由此带来人们对时空区隔和关系疏离的忧思。不过,信息传播技术为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了技术支持。受访者 A01 和丈夫目前在郑州经营着一家川菜馆,夫妻二人的孩子和父母都住在周口的乡下老家。她向我们述说了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为自己交往场景带来的改变,这为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如何重塑“集体时间”提供了启示。
在 A01 的经历中,公用电话是早年和远在家乡的人进行联系的主要方式,但基于公共传播工具的交往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性,“无法随时随地使用”“不能想聊多久就聊多久”是最突出的问题。同时,因为空间区隔、工作忙碌以及有限的媒介使用机会导致“集体时间”缺失,也为远离家乡的她带来了焦虑和孤独:
“我大概是 2003 年出来打工的,最早去的是广东那边儿,那时候都还没有手机,想联系家里人是不容易的。当时工厂宿舍外边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做完每天的工作后,最期待的就是听到有人喊我,说我家人来电话了,然后赶紧跑过去接。不只是我,其他工友也是这样的,我们都很想家,特别怀念和家人还有老家的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经常一起玩,一起去逛逛镇上集市。出来打工后这种分开的感觉很难受。”
购买第一部手机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我最早买的是诺基亚手机,没有特别的功能,就是用来打电话、发短信,跟咱们现在的手机肯定没办法比的。”
这位受访者的案例启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信息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离散的时间结构、进而重新创造“集体时间”。一方面,智能数字装置的社交可供性允许使用者建立实时、同步的连接,为分隔在不同地域的人创造了更多交互的时刻,也提供了更自由、灵活的时间选择。另一方面,纷繁的数字媒体应用革新了在场交流的形式,作为部落体验的“集体时间”回归日常生活,共时性的交往重拾部落时代的记忆。
对于分隔在不同地方的人们而言,缺席家乡的传统节日和庆典通常是无奈的选择,但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传统仪式的云端展演提供了契机,地点在信息传递中的决定性意义亦被改变。受访者 A08 讲道:
“去年我和一起在郑州打拼的女朋友结婚了,当时我就想着怎么让不方便到现场参加的亲人、朋友也能跟我们分享喜悦、一起见证。我决定开个直播间,这样就让外地的亲友加入进来。事实证明效果不错,我们顺利完成了婚礼。设置了一些直播互动环节,里面的弟兄们为我和她送出真挚的祝福,有人还刷了礼物。”
对于居住在冉屯新村这种由原市郊乡村拆迁改建而来的地方的村民来说,居住环境改变造成的集体时间减少,并未为他们的人际交往带来困境。受访者 B01 说,她和原来的朋友们已经通过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建立了稳定的连接,不仅会进行诸如游戏“开黑”、抢红包等线上集体活动,同时也将媒介作为征服空间距离、组织线下交往的技术工具: “我个人不太喜欢在手机上说话,但如果他们叫我打游戏,我也陪着一起玩。但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聊天,所以经常用手机和大家联络,叫他们出来。”
此外,研究者亦观察到冉屯新村周围也有人搭台唱戏、载歌载舞、打麻将,这则是部分老龄居民找寻集体时间的方式。
上述几位受访者的案例表明,不论是玩游戏这种新型在线娱乐社交活动,还是结婚、出嫁这种传统仪式的云端展演,都表明信息传播技术为人们重新找回“集体时间”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而人们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征用”技术的可供力,不仅让遗失的部落体验重新焕发生机,也带来了互动和交往形式的创新。
( 二) 共享的领域: “三重部落空间”的技术与社会建构
在部落化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空间的共享”指涉了参与、亲密和集体等概念范畴,是部落意识得以形塑和维系的条件之一。数字传播技术的可供性和技术的社会采纳,为乡村部落空间的重建带来了机遇,促进了 “三重部落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推动了信息、经验和知觉在部落空间的共享。
1. 家庭交往空间
背井离乡的务工者与家人珍贵的团聚时刻在每年春节档电视新闻的视觉呈现中屡见不鲜,这表明乡村家庭成员缺少共处空间这一问题已经为社会所关注。而传播媒介的创新与扩散,正在云端重新建构乡村家庭的交往空间。学者认为,对于出国打工和远嫁的村民而言,移动网络具有维系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网络与家庭空间再生产的功能。瑏瑡 家庭交往空间并不是意指客厅、起居室和卧室这样的物质场所,但也绝非抽象的概念想象,家庭空间可以通过社交群组来维系,依赖持续性的互动相处进行维系,并依靠其他媒介允许的连接形式嵌入日常生活。
受访者 A11 表示: “我和家人一般都用微信联系。我建了个群,把爸妈、老婆和弟弟一家人都拉进去了。现在微信用起来很简单,爸妈学学就会了。”微信作为一个提供亲密、温馨氛围的家庭交往空间,让外出务工者随时与家庭成员保持互动,对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基于微信群的中介化互动可能是面对面交谈的“替代性满足”,但这种社交群组确实能够创造“家庭的体验和感觉”,实现家庭共享空间的再生产。
2. 乡村/族群空间
中国乡村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共享着相应的文化观念、道德传统,生活在“时空同步”的部落场景中。随着时间的变迁,媒介和交通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传统共同体赖以存续的空间和场所,人口外流、土地拆迁令后,“时空同步”的场景趋于松散、瓦解,乡村共同体面临生存危机。但这种情景在智能媒介普及后有所改善。人们可以利用智能媒介建构属于乡村和族群共同体的交往空间,共享信息、生活和经验,加强彼此间联系。
访谈发现,某些乡村已经在村民提议下建立了诸如“乡村大家庭”“乡里乡亲”这类允许全体村民加入的社交群组,打造了即时互动的乡村空间。据受访者 A01 介绍,她所在村落的大部分人都加入了“乡里乡亲”群。其中,青壮年占比最大,村里的老者和长辈也被邀请进群。从互动状态来看,群组中的信息交流在特定节日或事件发生之时最为频繁,平日也有一些重要通知发布。村里的青壮年是主要发言群体,长辈更多地扮演着“观看者”的角色,发言频率偏低。冉屯新村的社区和大队也建有微信群,这些群组主要作为居民接收通知和重要信息的渠道存在,具有明显的工具属性,而非情感交流的场所。这说明要想真正建立“深度卷入”的云端乡村空间,既需要乡村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对交往空间的准确定位和氛围营造。
3. 个性/趣缘空间
与集体化时代村民在身份、兴趣上呈现的趋同属性有所不同,如今人们发挥个性、以趣为缘,打造基于个性或兴趣的交往空间,推动了部落领域在崭新技术语境下的重塑与再造,进而形成新鲜、多元、共享的部落经历。
受访者 A02 在访谈中说起了自己加入的趣缘群组———“爷们儿红包群走起”:“这是村里附近几排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建的群。虽然名字叫红包群,其实也没有天天发红包,更多的是聊一些彼此感兴趣的事儿,或者喝酒了之后给里边儿吹吹牛啥的,毕竟大老爷们嘛。如果村里其他人想加进来,我们也持开放态度。” 此外,有几位受访者也表示他们会和亲友、同乡一起创建或加入“游戏开黑”“带货”“农产品推广”和“房屋租赁”等基于个人兴趣、需求的线上主题群组。
“集体时间”的重现与回归,以及“三重部落空间” 的技术与社会建构,表明乡村的交往时空正在技术与人的双重作用下实现重新组合,身处异地的人们逐渐卷入“时空同步”的部落场景,再现、延伸了遗失在历史浪潮中的部落体验,也让重建乡村的愿景变得清晰可见。
五、重塑社会关系: 信息传播技术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革
部落场景在云端的重建并非意味着乡村的重新部落化已经完成,相反,这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变革的开始。乡村作为涉及信任、团结、认同等概念的熟人社区和多元共同体,在社会文明变迁中面临着关系疏离、代际隔阂和认同缺失的困境。本部分将围绕支持、沟通和认同,探讨信息传播技术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革,从而揭示社会关系层面的重新部落化。
( 一) 重建支持网络: 社会资本在云端的流动与共享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网络、规范和信任,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瑏瑢对于具有雄厚社会资本的社区而言,关系紧密、互动性强、信任程度高的交际网络可降低成员的交际成本,成功的合作经历也为将来的合作奠定基础。社交媒体在社会资本的整合中展现了潜力,对于乡村这种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衰落的熟人社区而言更是如此。
受访者 A12,一位在郑州管理火锅店的经理表示,加入微信群组为自己提供了支持网络:
“微信群里主要是老家的乡亲,有些熟悉,有些关系比较淡。不过,如果你在里面求助的话,大家会尽可能帮你出力。在郑州的时候,会请大家帮我推广一下火锅店,然后群里人分享的新闻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发展和现状。之前还有人请大家找人,估计是经商的缘故吧,后来有乡亲在群里把那个人的微信名片发给他了。我们自己能力有限,但如果依靠大家的力量,有些问题也就不那么难了。”
透过 A12 的表述可以看出,微信群在此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表征,整合、收编了离散的资本,为社会资本在云端的流动与共享提供了稳定的场所。成员在乡村社交群组中通过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援、信息支持和关系分享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体验到个体与部落之间、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了部落信任与团结。
在技术与社会力量重构的时空场景中,不仅以往遗失的人际关系能够重新连接,个体也可以实现自身关系网络的延伸与拓展,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受访者 A09 说道:
“自从 5 年前来郑州打工,我和阳哥也就没再有什么联系了,听说他去了别的省。后来大家都买了新手机,微信也会用,就有人提议建一个大群,我看阳哥也进群了,和他加好友后说了很多。当然,还有一些之前不怎么玩的老乡,因为吃鸡( 即《和平精英》游戏) 成为了朋友。”
( 二) 助力代际沟通: 技术反哺与乡村数字代沟的弥合
信息传播技术嵌入社会后引起新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数字鸿沟便是其中之一。在家庭层面,数字鸿沟则表现为“数字代沟”,即父母( 亲代/传统世代) 和子女( 子代/E 世代) 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瑏瑣 作为乡村社会的初级单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可能影响村落的团结和凝聚力,因此,如何弥合日益扩张的数字代沟成为乡村重新部落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数字沟”面前,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往往被视为一种区隔性因素,在本已存在隔阂的代际之间又筑起技术铁幕。媒介技术确有“区隔”的一面,但同时也具备“连接”的力量,而来自青年一代的技术反哺正是发挥这一力量的关键。作为一个知识传递、共享和探索的过程,技术反哺既体现在晚辈帮助长辈掌握数字装置的功能和基本知识上,也体现在助力长辈有意识地运用传播媒介改善自身的信息环境、进而提高生活质量的努力上。
受访者 A14: “为了能更方便地和爸妈联系,我给他们买了一部还算操作简单的手机,两位老人家共用。一开始我教他们使用电话、微信等功能,后来他们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东西看,有时会分享给我。虽然大家说老年人都是健康养生文章的忠实粉丝,但也不全是这样的,我爸妈有时会跟我分享一些家乡的新闻、新变化,或者郑州的一些事儿。”
受访者 B10: “不久之前给我妈买了这个手机,然后教她如何发微信、怎么打微信电话、看公众号,还有搜索软件、视频软件的使用我也会跟我妈说,不过她对视频不太感兴趣,还是喜欢看公号文章。虽然她还没有完全掌握手机的操作,但这对老人和孩子之间的沟通还是有明显帮助的。”
透过访谈文本可以看出,在重新部落化的语境下,技术反哺正在作为一种沟通和团结机制发挥着作用,它勾连了乡村不同代际之间离散的知识结构和媒介体验,为信息、知识和经验在代际间的共享创造了条件,这有益于塑造部落成员之间的亲密感和团结感,从而提升乡村作为“部落化社会”的内部凝聚力。
( 三) 守护乡愁记忆: 乡村文化与部落认同的再造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地域形态和空间格局,撕裂了乡民的生活空间和仪式空间,进而使得乡村记忆的承载媒介及其稳定性的时空机制就此失效,城市规则和文化话语对乡村历史、传统的排斥也割裂了乡民与其过去的连接,中青年主流群体的高度“缺场”则中断了记忆的传承实践。
但新兴媒介技术为乡村记忆的书写、传承与再造提供了“庇护之所”。在对受访者 A03 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微信朋友圈正在作为“部落记忆的流动展板” 发挥着作用: “像我们这样身在外地的人肯定都很想家吧。用了微信之后,就加了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他们有的现在也给外边打工,所以我们都挺忙。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经常说话,但我会默默关注他们的朋友圈,尤其是他们发的家乡的图片、视频。没事的时候看看他们拍的这些东西,能让我想起很多家乡的事。”
在此,微信朋友圈作为“部落记忆的展板”,组织、呈现了记忆的信息流,实现离群个体与部落记忆的再勾连,将务工、远嫁的成员重新纳入“乡愁”的神话叙事中,唤起个体对部落的情感和回忆。
受访者 A02 说: “我一年和媳妇回不了几次家,很担心会把老家的感觉逐渐忘掉……在店里比较闲的话,我会刷刷抖音,特别希望看到讲我们老家的视频,或者是在我们村里拍的。有时候我也主动搜索,在百度和快手上面……如果能在最美乡村评选中看到我们村,那我一定很开心,而且会想办法拉票。”
从另一方面来看,媒介技术所具有的存储、检索与表征功能,也使其成为了再现和延伸乡村记忆的数字装置。受访者 A05———42 岁的社区保安,向研究者讲述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的记忆力没有小时候好了,记东西没那么清晰了。不过还好,现在我可以把家人的照片存到手机相册里,平常发的信息、语音只要不删,也就不会丢。有时候想儿子了,但他还在忙,我会听听之前的语音。这不,前几天给我发了一长段生日祝福,虽说现在岁数大了,不爱过生日了,但我还是很感动……家庭和我们村的群里也有一些视频,这都能帮助我记住家乡。”
研究者在访谈中还发现,信息传播技术也作为乡村文化符号的传承载体发挥着作用。冉屯村地处郑州西郊,保留着带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但由于口语的易逝性和使用主体的减少,方言曾经一度面临着传承的困境。村民 拥 有 手 机 之 后,情 况 发 生 了 改 变。受 访者 B03:
“我们这儿有不少人喜欢发语音,说着外人可能听不懂的方言。我和朋友聊天打字的时候,也会刻意地用一些代表方言发音的文字,比如要跟别人说‘没有’,可能会打一个‘牟’,诸如此类。” 由此可见,借助媒介技术,人们把速朽的部落经验转换为数字记忆,从而克服了记忆的易逝性,使乡村记忆在时空中延伸,为社群所共享,进而促进文化和认同层面的重新部落化。——论文作者:郑素侠 杨家明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