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0-02-05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302次
摘 要: 摘要:资源环境紧约束下,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加剧,有限的土地资源只能在耕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之间进行转换。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对不同土地用途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将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建设用地排在首位,但在垂直管理体制下,耕地、生态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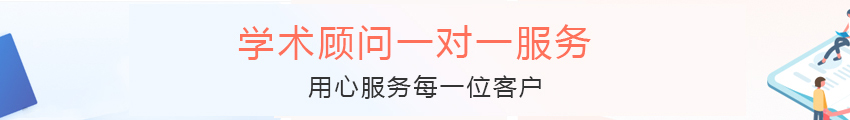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资源环境紧约束下,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加剧,有限的土地资源只能在耕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之间进行转换。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对不同土地用途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将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建设用地排在首位,但在垂直管理体制下,耕地、生态用地等控制指标的达成与否关系到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的核心利益。在横向与纵向的双重约束下,同一层级不同职能部门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冲突,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当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出现土地利用冒险行为,如将基本农田转变为生态用地以获取绿色政绩,将生态用地转变为生产力极低的耕地,这些行为不利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最大化。整理存量建设用地、发展可持续集约农业、系统管理自然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类之争。

关键词:资源环境;土地竞争;注意力竞争;冒险行为;平衡策略
粮食生产、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都对土地资源有所需求,且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土地资源成为各种用途激烈竞争的焦点。资源环境紧约束下,有限的土地资源只能在耕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之间进行转换。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导致我国优质耕地持续减少,虽然我国依靠集约化农业技术、过度利用耕地和开发生态用地等方式保证了粮食可供量的稳定增长,但其所追求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是一种短期行为,这种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而生态环境又反作用于粮食生产系统。在“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土地利用三难困境下,如何平衡土地资源利用的短期效率与长期可持续性?笔者拟从需求视角分析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驱动下的用地竞争,进而从供给视角分析激励与控制下土地资源实际控制者(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排序,以及供需冲突下不同职能部门的土地利用冒险行为,以期为平衡土地利用提供对策。
一、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驱动下的用地竞争
(一)建设用地:经济增长驱动的土地需求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为了激励地方发展,将经济增长指标置于官员政绩考核的首位,形成官员晋升锦标赛,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外在激励。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财权上移”、“事权留置”,财政缺口使地方政府致力于财政收入增长,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激励。在政绩考核与弥补财政缺口的双重激励下,各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官员升迁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形成由地方政府主导“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主要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其中,资本和劳动力基本实现市场化,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主要是土地。由于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建设用地的政府管制、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及对一级市场的垄断[1],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实际控制者。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地方政府过度占用土地资源,将耕地、生态用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发展城市经济。一方面,地方政府竞相为制造业投资者提供低成本土地,通过低价或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建立大批工业园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开发区,通过高价出让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增加财政能力,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吸引资本[2]。2009-2016年,我国建设用地面积大幅提升,其中,城市用地从5291.4万亩增至6508.7万亩,建制镇用地从5584.1万亩增至7638.3万亩,交通运输用地从11912.9万亩增至13273万亩。
在既有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收入来源结构下,地方经济增长存在严重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修订版)》预测,205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80%以上,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将不断增长,城市将不断蔓延。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带来自然资源浪费、耕地减少、污染加剧等负面效应,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对占用土地资源有强烈需求,而随着乡村生产方式和消费需求升级加快,乡村用地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乡村建设用地需求强劲。随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3],设施农业项目用地需求强劲,现代农业生产所需的配套项目用地需求大幅增加,农业功能拓展催生农村新型建设用地需求,农村公共设施用地需求也不断增长。由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以及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在各种土地用途中将建设用地排在首位,选择优先满足城市经济增长的用地需求。而乡村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随着产权的不断完善,对农村土地用途转换的自主权较大。因此,在不能有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情况下,面临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对建设用地的强劲需求,地类之间的转换压力巨大。
(二)耕地:粮食安全驱动的土地需求
1978-2016年,我国人口从9.63亿增至13.83亿,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至6.16亿吨,人口增加并没有降低人均粮食产量。我国食物不足发生率从1990-1992年的22.9%降至2014-2016年的9.7%,食物不足发生率下降速度快,在减轻饥饿方面成绩显著,这得益于“绿色革命”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粮食可供量大幅增加。但随着“绿色革命”技术的收益不断递减,粮食单产的继续提高面临重大挑战。以我国口粮生产为例,虽然单产从1995年的4659公斤/公顷提高到2016年的5990公斤/公顷,但单产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趋势。另外,以石油农业为主导的农业技术进步通过在耕地上大量投入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等实现粮食短期产量的大幅提升,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污染,进一步限制了单产的提高,对粮食质量安全也造成负面影响[4]。而随着人口高峰期的到来和需求层次的提升,对粮食可供量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对粮食质量和营养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年(修订版)》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约14.41亿人),其后有所下降,但2050年仍将有13.64亿人,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口粮的人均消费量增速加快,对肉类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粮食安全有四个维度:粮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5],因此,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提高粮食可供量,也要提升粮食质量、营养和维持供给的稳定性。我国刚性增长的巨量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长需求和对粮食质量的更高需求,对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
粮食生产是资源约束型生产,本质的约束资源是耕地,粮食安全的核心是耕地安全[6]。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石油农业负面效应的突显,耕地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耕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耕地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2009-2016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695.4万亩;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从9.80等变为9.96等,低于平均等别的耕地占比明显上升。另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这将导致中国每年减少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应[7]。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下降、耕地土壤流失、耕地土壤养分失衡等问题也很突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下降,继续大幅度提升单产受限,增加用于粮食生产的优质、无污染的耕地面积的压力将会增加[8]。在此局面下,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耕地的控制力度,要求地方政府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中央政府期望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以保护优质、无污染耕地,避免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改变用途,确保粮食安全。
(三)生态用地:生态文明驱动的土地需求
在经济增长和粮食生产对土地的需求同时增加时,土地转换的压力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发展经济需要占用耕地,中央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则严格控制耕地。在激励与控制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双重开发来同时满足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对其耕地保有量的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占用优质耕地以满足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将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用地开发为耕地以实现耕地数量平衡。2009-2016年,我国园地面积减少818.3万亩,林地面积减少1562.2万亩,草地面积减少1547.1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减少669.9万亩,田坎减少311万亩,盐碱地、沼泽地、沙地共减少421.9万亩。双重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建设占用耕地使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自然社会耦合系统,系统内物质流、能量流均发生显著变化,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相应改变,进而产生城市热岛、大气污染、雨洪灾害等生态环境问题;而为了实现耕地数量上的平衡,又将生态服务价值高的林地、湿地、草地转换为生产力极低的耕地,这进一步导致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破坏,进而可能影响生产力和土地供应,形成潜在的恶性循环。另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也很显著,为了减少粮食对耕地的需求压力,通过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虽然短期内能提升粮食产量,但这种生产方式破坏了生态环境,不利于保障粮食可供量的长期稳定性。
作为一种提供必要生态系统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用地在维持生态平衡、保障国土生态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在保证建设用地和耕地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数量大幅减少,质量也急剧下降,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9]。另外,随着生态文明的深入推进,一些具有生态功能的土地被多年大量占用后,开始受到重视,公众对生态用地的需求激增。中央政府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增长和粮食的双重需求压力下,中央政府开始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严格保护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用地,严禁随意侵占或破坏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生态用地重要性突显。
二、冲突与冒险:职能部门的土地利用行为
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对土地资源都有强烈需求,但土地资源供给是稀缺的。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利用正向激励机制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而通过负向激励机制控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面临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激烈竞争,作为中央政府多任务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如何安排建设用地、耕地、生态用地的优先序,在实际土地利用中如何采取策略?为了切实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中央政府对国土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那么,国土资源部、环保部能切实履行其职责吗?当不同土地用途之间存在严重冲突时,不同职能部门将如何行为?下文将对供需冲突下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一)横向与纵向双重约束:职能部门竞争政府注意力
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驱动的竞争格局下,有强激励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生态是负向激励,没有完成任务将受到惩罚,因此,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上将采取策略性行为以取得合法性。为了切实保护耕地与生态用地,中央政府在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以加强控制。但从权威角度看,对于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上级党委政府具有实质权威,上级政府具有正式权威,而上级职能部门仅具有象征性权威。政府是强势委托方,除了掌握人事、财政和行政等重要资源,还对潜在配合弱委托方工作的其他部门有实质影响力。换言之,如果不依赖强势委托方而只凭借职能部门自身力量,其工作往往难以推动[10]。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长官对不同土地用途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将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建设用地排在首位,由于地方政府掌握地方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国土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工作需要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因而,国土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需为地方政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用地提供合法性,但这两个部门也处于纵向控制之下,耕地、生态用地指标的完成情况,决定其核心利益,因而,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为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由于政府权威,用地竞争演变为耕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竞争,地方国土资源部门与环保部门、林业部门等不同职能部门只能通过竞争政府长官注意力的方式获取土地资源,以超额完成上级职能部门的任务。
职能部门竞争政府注意力的策略主要有四种:一是显著性。组织处理事务的机制之一是显著性,即对显著或生动事件赋予很高权重,而对不显著事件赋予较低关注。国土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等职能部门会从不同角度强调本部门任务完成情况对地方的重要性。二是强调紧迫性。紧迫性反映了时间压力机制,职能部门竞争政府注意力的过程实质就是与政府进行谈判,而影响谈判过程、谈判能力、谈判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压力。时间压力越大,越能吸引政府注意力,如当接近土地利用规划的结束期,而当地的耕地保有量没有达到上级要求时,那么,国土资源部门强调紧迫性能获取政府注意力,当地土地资源短期内将向耕地倾斜以通过上级部门的检查。三是数据可靠性。在竞争政府注意力时,职能部门强调本部门任务的显著性与紧迫性需要可靠数据的支撑。四是比较机制。职能部门通过横向对比其他地方与本地在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上的差距能引起政府长官对本部门的注意。由于晋升机会是有限的,上级政府在考核下级的绩效和表现、决定提拔谁的时候,必然采用某种程度的“相对绩效评估”。如何使自己的政绩高过竞争对手是获得政治晋升资本的重要途径[11]。在晋升锦标赛下,虽然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增长,但对政府长官政绩进行排序时,如果一个地方的耕地、生态保护明显好于其他地方,那么当经济增长指标差别不大时,这个地方的长官在晋升锦标赛中可能脱颖而出,因此,进行横向比较是职能部门吸引政府官员注意力的有效策略。
推荐阅读:发表生态论文的SCI期刊
如果职能部门能在“注意力竞争”中取胜,那么,在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建设用地后,土地资源将向这一职能部门倾斜。粮食安全得到政府高度关注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始实施,国土资源部门在职能部门中地位高,虽然地方国土资源部门首先要满足地方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但之后,耕地是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国土资源部门可以通过开发生态用地实现耕地数量平衡。而当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政府的关注时,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开始实施,环保部门在职能部门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有刚性需求,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制度对耕地、生态用地进行严格保护,在地类相争、政策冲突明显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平共处”难度大,职能部门为了通过上级部门的检查将采取冒险行为,如玩数字游戏、双重开发、生态用地占用基本农田等,这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
(二)职能部门的土地利用冒险行为
第一,数字游戏。在地方政府的实质权威和正式权威下,国土资源部门首先要满足地方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在后备耕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通过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的检查,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部门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冒险行为。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求建设占用耕地需补充相应数量与质量的耕地,通常情况下,占用耕地的单位缴纳耕地开垦费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补充耕地,国土资源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为了给建设用地和占补平衡腾挪出足够的空间,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部门利用信息优势,将耕地和基本农田划到“山上”、划进“水里”,甚至划到存量建设用地上。有些地方为了实现耕地数量上的占补平衡,将荒草地、学校、农民建房等土地作为新增耕地验收入库,这导致验收后的新增耕地不具备耕作条件。更有甚者,以灾毁为由,将原本为耕地的土地变更为滩涂地,继而谎报通过复垦成为新增耕地。为了同时满足地方经济增长的土地需求和上级职能部门对当地耕地数量的要求,作为耕地保护者的地方国土资源部门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编制立项材料等方式实现表面上的耕地数量平衡,编制“漂亮”的统计数据以通过上级职能部门的考核,为地方政府占用耕地取得合法性。只注重统计数据上的平衡掩盖了优质耕地不断流失和耕地红线被蚕食的严峻现实,导致“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变为“数字游戏”。
第二,双重开发。当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在“注意力竞争”中取胜,耕地成为建设用地后最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可以开发生态用地补充耕地实现耕地数量占补平衡。耕地占补平衡实质是双重开发,一方面,建设占用耕地,满足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所需用地,国土资源部门能从地方政府获取充足的财政资金并得到其他部门的有效配合;另一方面,通过开发生态用地补充耕地能满足上级职能部门对当地耕地保护的要求,这对地方国土资源部门而言是一种占优策略。但双重开发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些地方为获得建设用地审批,千方百计扩大补充耕地面积,在不宜开垦的生态区“拓地”,将不适宜开垦的生态用地变为耕地来解决批地的燃眉之急,甚至将一些陡坡和林地、湖泊、沼泽等不宜耕种的土地盲目开发利用,将位置偏远、生态脆弱的地块用于耕作,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效益损失[12]。另外,这种双重开发对粮食安全也有负面影响,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为优质耕地,而通过土地开发复垦补充的耕地多位于丘陵山区、低洼易涝、耕作条件差的地方,农民对新增耕地的耕作积极性低,造成耕地的粮食产出能力下降。
第三,生态建设占用优质耕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一些地方环保部门成功吸引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在土地利用排序中生态用地重要性突显,环保部门与国土资源部门竞争土地资源的能力增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将以往城市“摊大饼”式开发的用地思路和方式直接“拿来”,在城市周边、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建设城镇生态公园、景观工程、绿化工程等生态项目,这些生态项目大量占用耕地甚至基本农田;另外,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及休闲旅游等生态项目也大量占用耕地(基本农田)。环保部门为了避免与自然资源部门的直接冲突,采取策略性行为增加生态用地,如为规避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通过给予农民价格补偿的方式将耕地转变为林地或绿化用地,而不变更土地利用现状,依旧按照耕地和基本农田进行管理,被占用的耕地不再承担粮食生产功能,造成耕地隐性流失[13]。为了追求绿色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在土地利用中出现冒险行为,将优质耕地转变为生态用地,造成优质耕地大量减少、耕地保有量不实,耕地保护红线受到威胁,粮食安全承受巨大压力。由于环保部门竞争能力增强,生态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竞争加剧,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填塘造地”与“挖田造湖造林”并存的现象,职能部门的分割与竞争导致双重土地利用冒险行为出现,这给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