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18-02-26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547次
摘 要: 很多的童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在《白雪公主》这一典型的童话故事中,这则童话对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再现超越了刻意否定和丑化王后的传统叙事空间。通过镜子的奇妙体现判断主体,将国王及其欲望充分体现出来。国王的现身让童话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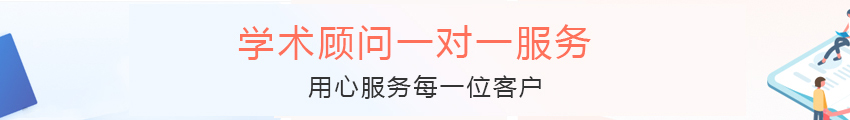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很多的童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在《白雪公主》这一典型的童话故事中,这则童话对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再现超越了刻意否定和丑化王后的传统叙事空间。通过镜子的奇妙体现判断主体,将国王及其欲望充分体现出来。国王的现身让童话最终融入了反面人物的文学潮流中,并成为反映至今仍留于多种现实生活与人际关系中的缺陷工具。
关键词:童话,社会伦理,意识形态

隐喻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是以人类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经验领域的某种重要认知活动。[1]28经典童话中的许多隐喻就是这样的重要认知活动。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千百年来的人类生活经验与人际关系,但其中再现的某些普遍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等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它对社会现实的再现与艺术虚构包含多重隐喻意义。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在《真相的捍卫者》一文中也指出,早期愚蛮社会因疾病或孕妇生育死亡率较高,导致当时的家庭生活缺失生母成为一个常见社会现象。但尽管许多文学作品曾一度对此做出反应,而读者还原其中的“真相”却并非易事。[2]95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过于看重这则童话对身为继母的王后充满道德寓意的精彩反讽与抨击,却忽视了洞察其中一再出现的隐喻“谁是最美丽的人”[3]2所折射的错综复杂内涵。从拉康与福柯等的视觉理论视角去看,这一话语是《白雪公主》中的重要隐喻性语素。它隐含的“真相”使其中遭受迫害与追杀的白雪公主并不令人同情。恰恰相反,她的迫害者与追杀者——王后的人生实质上更具悲剧性。其悲剧的起因在于一面会说话的镜子奇妙地成为了“美丽”的判断主体,导致陷入“美丽”欲望偏执的王后不仅无法容忍他人“美丽”镜像的存在,而且她对自我的虚空幻想也难以自控地停留在了换装癖与杀人狂的心像诱惑阶段,最终走向可悲的毁灭。
王后的悲剧表明,她从未看穿镜子符咒般的隐喻断言是其自身冥想幻象与现实对应物的载体,即镜中之像满载着国王这一他者的欲望,向她呈现的始终是自我虚构与欺骗。在对其“美丽”欲望祛魔的过程中,童话一方面尖锐地鞭挞了继母的狠毒与施虐癖,将她生动地符码化为充满贬义的反面类型人物。另一方面,童话初版与后来的6个改编版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还暴露出原作者和多个无名改编者对缺席在场的国王乱伦,以及遵循外婚制的王子恋尸癖等邪恶人类欲望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手法。这些因素使这个实则有关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的童话故事跨越漫长的历史与叙事空间,隐晦地成为再现至今仍留存于多种现实生活与人际关系中人性缺陷的工具。
一、 王后的“美丽”——个体形象与主体幻象对应的心像
在童话中,会说话的镜子虽然在一开始满足了王后评判自身“美丽”与否的视觉期盼,但它呈现的却是隐藏于其内心冥想中复杂隐秘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使她偏执地不断依赖镜子作答的追问—— “谁是最美丽的人”——给童话故事的“美丽”一词增添了特殊内涵。该词将她追求表现视觉满足的容貌美与“美丽”镜像喻指个人心理满足的欲望怪诞地结合,碰撞出人性异化的弦外之音。
從特里·伊格尔顿曾提出的,语言“更是权力和行动,而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4]349来看,王后的语言不仅是反映“权力”的社会结构,以及表现“行动”的人际关系,更是使这一追问产生语义逆转的工具,即她的“美丽”镜像密切关联着各种权力欲望,并能够兼具商品价值和交际作用等。而根据拉康指出的,人们在日常经验的象征效用阴影中,可以粗略地看到心像被遮掩的“面影”,镜中之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入口”[5]3等观点则可发现,王后的追问敞开了一道被 “美丽”面影遮掩的人性阴影,并以表面上庸俗无知的话语形式抽象地与整个故事相连,隐晦地建构了并不囿于她目光所看到的事物之中的事物。
倘若以福柯“语言的价值在于它是物的符号”[6]46等观点来看,王后的追问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物化语言符号,隐晦地表征了她内心时刻充满占有“美丽”的强烈欲望与失去它的恐惧,表明高贵一时的她不过是王宫里一个临时的人体模特儿,除了“美丽”以外一无所有。为此,童话表面的叙述模式使这一语言符号的意指功能指向的不是拥有,而是发现、判断与欣赏“美丽”的主体。它如同魔咒一般,将王后禁锢在一个摇摆不定的“美丽”欲望循环当中,最终导致王后看到的镜像中的不可见性浮现出来。
这一不可见性便是国王的欲望在王后心镜中的投射。作为国王视觉霸权中的“美丽”客体之一,王后显然不可能对抗成为“美丽”参照点的任何镜像,因为形成这些镜像的女性视觉身体无疑都在按照国王的指令而受到约束与标记。会说话的镜子集国王的发声器官与视觉器官于一体,既为国王的喉舌代言,又表现他对美丽女性的凝视目光,使王后心中的“美丽”镜像最终成为表达国王欲望所借助的一个关键语词 在分析巴尔扎克的《朗热公爵夫人》中,彼得·布鲁克斯也曾指出,“女人的身体按照女性欲望的指令而受到约束和标记,从而变成叙述中的关键词”。见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与它相关的任何其它话语甚至行动实质上都是在叙述与重复国王的欲望,留给王后的则只有不断被动地怀疑与分裂自己的“美丽”,以及持续返回自我对它的偏执虚构当中。
国王的隐秘现身丰富了王后“美丽”偏执的内涵与根源。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维雷娜·卡斯特指出, 在童话中,“美丽”和“幸福”是同义词[7]189, 因为婚姻从来就不只意味着人应该履行的一个“社会规范”,它要表达的是一种“幸福的结合。”[7]190由此可以看出,王后的“美丽”追问其实并不自私。相反,它能够从表面上是她保持容貌美的庸俗口号,潜在地转变为她自然而合法地捍卫婚姻幸福的正当语义意识表达,也就是拉康所说的“真实在主体中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本能的合谋”[5]12。
换句话说,王后因国王的凝视而分解与重组了她对自身“美丽”的向往,以及对他人“美丽”的排斥,并导致她对其他女性的“美丽”产生出受冷落的原生嫉妒。原因就在于,这一“美丽”与她本能的合法“幸福”密切地接合,而其他人的“美丽”则是对二者的威胁。王后无疑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美丽”镜像被取代,自己就将只能无奈地接受不可能对她有利的挑战。因此,白雪公主成为“美丽”镜像的宿主使王后萌发了杀死她并吃掉她的心 这一点在不同版本的译本中说法不一。例如,较早的魏以新译本是猎人杀死一只小猪,取出了它的肺与肝交给王后。见《格林童话全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53页。张亦朋的同名译本是猎人杀死一头小鹿,取出了它的心和舌头。见《格林童话全集》(上下),启明书局1946年版,第229230页。 ,复原自身青春美丽的可怕冲动。
但一心想迅速采取行动,消解自我镜像被公主取代的王后,却似乎落入了唯恐“美丽”被阉割以及阉割他人“美丽”的困境。由此产生的欲望偏执和心理断裂使她不可能超越个人醒悟阶段,实现她以长辈和母亲身份向人性的回归。这导致她对“美丽”原本单一的幻想停滞在无法满足自我欲望,转而嫁祸他人的心像诱惑阶段。外表纯潔的公主则成为她的致命对手,无情地站在了她婚姻保卫战的对立面。为此,除了一时的荣华富贵,“美丽”为王后带来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保持自我容颜与阻止甚至扼杀他人“美丽”的二元对立悖论。而被这一悖论悬置起来的欲望联想随即成为王后心中的一面镜子。
在“美丽”欲望力比多激发的征服和死亡欲望驱使下,丧失伦理与道德判断的她三次乔装,先后装扮成丑陋的商贩、老太婆与农妇等,试图戗杀与她媲美的公主。而她的无情追杀却引来了猎人及七个小矮人的同情,甚至王子的反抗。在无路可逃的反追杀过程中,她反而成为被追杀的对象。虽然她施展伎俩 即一般版本中使用的“witchcraft”(巫术)一词,可参见Jacob and Wilhelm Grimm, Selected Tal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4,第78页。 一再脱险,但这种自我阉割式的追杀却没能促成她对镜像的醒悟,反而使她执迷于展开受心像诱惑的一轮又一轮疯狂行动。
从社会伦理的常规角度去看,冷酷无情的王后最终是输在了自己丧心病狂的虚空幻想上。因为她始终没有醒悟,与宝贵的生命和善良的人性等相比,她渴望的“美丽”无足轻重。为此,心理失衡的她不仅持续人格断裂,而且越来越多地失去“美丽”的容颜,逐渐变得苍老甚至狰狞。迪斯尼版的《白雪公主》等现代影视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王后无视人类博爱而导致其个体形象衰变的心路历程,而且通过所有救助公主的人甚至动物传播的仁道精神表明,王后毫不掩饰的残酷杀戮在使她自身内心的“美丽”镜像四分五裂的同时,还激发了众人对公主的同情。在所有童话版本中,一成不变地描写恶毒的王后最终遭受脚穿烧红的铁鞋致死的结局,就反映了恪守道德与禁忌的社会严厉惩罚残忍继母的普遍伦理态度。
但从童话语境的视觉实质与根源上看,王后的认知偏执与智性判断和反应则事出有因,并将国王代表的传统男权意识形态表露无遗。
二、 王后的欲望——主体想象与客体幻象对应的现实
有学者在《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一文中指出,黑格尔的关系性自我意识——主奴辩证法提供的一个重要关系式是——“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它只是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而拉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对此做出的新发现则悬置了这种可以延迟的欲望,使自我不再是由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组织而成的意识实体,而是一种超现实的幻象,架构的是一系列异化认同为基本构架的伪自我。
根据上述推论,多个版本的《白雪公主》虽然在王后建构自我“美丽”镜像的复杂历程及细节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对王后欲望的心理生成和人格逻辑表现却基本一致。其中最醒目的主旨表达是,不论王后渴望“美丽”的主体意识有多么强烈,在国王的凝视下,她的个人欲望往往都会丧失其主体性,并在被国王对象化的镜像关系中认同自我与他者。
这使王后对镜像的偏执可以进一步说明,在以国王为想象主体的场域中,转化为无意识视觉客体的王后还是自身主体幻象的对象,即她所想象的自己在国王眼中的形象。这一想象不断地悬置或延迟她先在的意识与欲望,迫使她在对超现实幻象的异化认同中架构自我认同的伪自我,最终目的是无条件地迎合与满足国王的欲望。为此,王后便是为国王这一多变他者的视觉快感构架的一副伪自我面具。会说话的镜子则是结合她所有心理视觉结果而产出的具体指涉物,不但复制着国王的欲望,呈现的也是其目光所看到的“美丽”对象。
通过转述幽灵般在场的国王“话语”,普通的镜子转化为一面魔镜,并仿佛以国王传声筒的形式使他开口讲话,成了其本人缺席在场的对应体与化身。他的现身使关于两个“美丽”女人关系的童话转变为表现镜子这一能指的视觉逻辑叙述。它使王后从能够思考的主体,先是转化为被国王凝视的客体,然后是被这一凝视超越的次客体。或者说,填补了国王缺失的伴侣,即白雪公主生母的空位之后,王后的人生轨迹就很快被一再贬低降格,最终蜕变为丑陋恶毒的老太婆。而这一悲剧过程产生的本质性源头又不断回指国王的凝视。
从拉康曾指出的,眼睛仅仅是某个东西的隐喻,或某个先于人眼睛的东西,即凝视的“前存在”[5]15 拉康更愿意将这个东西称为看者的“瞄准”。 来看,童话中魔镜呈现的对象,即王后凝视的前存在实质上是让国王心动的“美丽”女性。细心敏感的王后一定多次发现了国王目光游移的秘密与凝视规律。在对它们进行揣摩分析和暗中解读的过程中,她不自觉地成为国王目光的客体表征,不仅被这一主体所控制,而且被他目光中的期待同化。最终,国王的欲望成了王后的无意识欲望 拉康指出,“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 。在他君临一切的强力情感主宰下,王后伪自我的异化认同无可奈何地一次次质疑甚至否定自我美丽,接下来便被动地聚焦在被国王“瞄准”的对象上。
对王后而言,只有满足国王的欲望,其自我存在才能与其心理期待相一致。而国王的欲望却是难以揣测与满足的。王后对“美丽”镜像的执着追问,既表明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妩媚女性不计其数,又暗示她与国王之间存在着一种合法但又极不稳定的两性关系,随时可能葬送她未来的“幸福”。维护前者的欲望显然使她想方设法地保持与国王的关系。
对王后有利的情形是国王钟情并专宠于她,而置其他女性的妩媚于不顾。为了这一奢望,古今中外的上层女性能够借助的法宝往往只有自身的容貌。在童话中,王后铲除他人“美丽”镜像的企图显示了她想要实现上述奢望的逻辑独白。为此,她渴望保持的“美丽”,实质上就是要赢得国王的肯定和赞赏及其带来的“幸福”,而公主的出现则不仅使她难以梦想成真,而且影射了她必将面对的挑战当中最为艰难而又错综复杂的一面。
在《死亡与少女》中,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指出,男人的定义通常以其作为得到确立,而女人的定义则来自其容貌。所以男人注视女人,几乎能用凝视穿透女人的身体。[9]59从这一点来说,耶利内克与拉康关于图像或凝视的背后总是有许多目光[5]54的观点不谋而合。尽管二者可以让来自女性容貌背后的男性凝视颠覆女性天生爱美的无稽说辞,并说明王后“是为他人,即国王而生的”[9]17,但却不能在男高女低的传统社会地位划分上让身为男性与女性的國王与王后例外。也就是说,普通男性在传统上就拥有凝视与评判女性外表的特权,而国王与王后的特殊政治身份尤其会导致国王的凝视永远不可能产生驯服的“看”的功能。这使二者之间原本就不平等的性别定义更加倾向于王后的容貌。
因此,王后对“美丽”的偏执追求不仅突出了她对弱势女性社会身份充满恐惧的抗争,而且使这一欲望与身为强势男性的国王和他背后的权力划上了等号。对王后而言,失去容貌美就等于失去婚姻幸福和与此密切关联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一逻辑使“美丽”成为一种换取“幸福”的可交换商品,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后者等价。但对它永恒占有的欲望则不仅过于奢侈和无望,而且会招致诸多的苦难与危险。
镜子对白雪公主“美丽”的宣告标志着这一苦难抗争的开始。而痴迷于自我“美丽”的王后不可能轻易认同公主,因为允许后者存在就必将解构其自身所偏执的“幸福”神话。而要还原自身的“美丽”镜像,则只有置换被公主颠倒的“美丽”主体。在童话的语境里,这一置换方式就是发生在继母与继女之间不择手段的追杀与反追杀。
三、 看穿“谁是最美丽的人”——现实的祛魔
认清镜子呈现的“美丽”镜像是王后所有心灵欲望增生扩散的内爆结果之后,童话对王后所处社会语境的多方映射才能得到现实祛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语教授杰克·齐佩斯曾指出,格林兄弟收集与研究民俗或者童话,实际上是将它们作为手段和载体,揭示把德意志民族联结起来,并表现其法律和习俗中的辞源学和语言学的事实。而口头传述的民间故事一经文本形式被解说与传播后,其中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视角便有可能被泯没或置换。但格林兄弟建构的民众言语形象以逼真的创作手段,即以“纯洁的手”解读和破译了民间传说,其中产生的现代性特征与历史起源,在让读者感受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同时,使某种社会文化现实尽可能客观“无我”地被重构在了民众中间。
这一当代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与俄国著名民间文学研究者普罗普的观点相吻合。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中,普罗普指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具有上层建筑性质的现象,保存了许多业已消失的社会法规、制度与生活的痕迹。因此,王后要求猎人杀死公主,取回她的心吃掉是将她当做了祭品,这仿佛是某种类似巫术的原始献祭仪式的一部分。公主第三次中毒后,救活她的王子来自远方,一见到她就情不自禁地要求将其带回家,反映的则很可能是封建社会前氏族社会里的“外婚制”现象。而七个小矮人公社式的相同生活起居方式,也影射了单身男子居住的“男性公房”。甚至,王后为了毒死公主而换装易容,制作有毒的梳子与苹果,则反映了人们的原始神话思维逻辑等。[11]89 普罗普还指出,民间文学的故事母题中有许多源自各种早期社会制度和法规,与《白雪公主》有关的就有孩子被送到或驱逐到树林里,改头换面和棺中美女等起源于整套授礼的活动,而王后最终被迫穿着铁鞋走路是关于死亡观念的系列等。
根据马克思所言,“若非人自身的影像,人从周遭的东西中是看不到什么的;万物都在向自己言说自身。它们的形象本身是有生命的,”[5]170《白雪公主》实质上以故事里的“美丽”镜像,隐秘地言说与重构了复杂的人类文明早期社会机制与人际关系。不过,其初版丝毫没有抹杀国王的恋童癖及其与公主的乱伦。它对有恋尸癖王子的描写,及其对后来表现出奢华癖的公主的拯救[3] 134等,也没有弘扬惩恶扬善的天道。质朴的初版似乎毫不掩盖生活当中存在令人惊悚的真相这一事实,它对多个人物异化命运的塑造也极大地质疑了人性本善的传统观念。
而在后来的6个改编版中,龌龊国王及其他人物的人性缺陷则显然被刻意忽略甚至抹煞。虽然在其他若干细节上也略微不同,但改编版与初版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均对王后进行了社会身份改写,将她从美丽、贤惠的生母这一自然身份,转变为恶毒丑陋的继母,同时还隐藏了初版对国王与王子私生活的直白描写中明确揭示的丑陋社会阴暗面。
为此,这一童话需要成人而不是儿童读者細心发掘表面上强调容貌“美丽”的故事中隐秘怪诞的现实真相踪影。在童话中,隐秘保存的四个蕴含传统象征意义的细节是可以帮助读者完成这一建构的。其一为“国王”是男性象征符号的原型,[12]15“王后”则如同喷泉、湖泊、海洋、河流、月亮等自然物,以及诸如篮子与杯子等器皿一样,是女性象征符号的原型。[12]12这使高贵的王后与隐秘的国王化身为拥有正常人类欲望的普通男女,而有关王室的童话则能够被普通化为搭建在民间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不寻常故事。
其次,王后制作有毒的苹果使白雪公主中毒,是由于苹果核形似女性外阴而具有“欢娱享乐”与“性交快感”的象征,它在“整个欧洲都是爱情、婚姻、青春、繁育、春季、长寿和不朽”的标志。[12]88作为欲望的主要象征符号,苹果还是“诱惑的化身”。这与基督教中的猿或者巨蛇口中的苹果象征着人类原罪[12]88等教义一致。为此,以有毒的苹果影射非法与变态的男女情爱关系显示了作者的高超智慧。
第三,内涵丰富的“镜子”是“真实、自视、纯洁、启蒙和先见之明”等的象征,据说能够将上天的神性反射到尘世。而且古人确信,邪恶之人挡不住镜子的照射,其在镜中也不能成像。艺术品中的镜子有时代表傲慢、虚荣或贪欲,具有否定含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镜子都是真理的象征,即民间所谓的镜子从不撒谎。在古代占卜中,镜子与魔法关系密切,具有推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魔力。[12]126镜子的这些象征性工具功能无疑可帮助后人理解《白雪公主》以虚构形式对远古文化的映射及其对现实的警示。
最后,远道而来的王子象征的“外婚制”则隐晦地强调了“乱伦禁忌”。这一婚姻制度是“针对乱伦的婚姻禁忌体系的最原始形式”[13]31,代表社会公开地把一种社会性赋予某种亲属关系,来阻止亲属间性结合的社会伦理。它同时还影射“接触禁忌”[13]43,不仅防范同一氏族男女间的性亲近,还旨在将个人良知与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崇高化,即升华个体性与非个体性之间的对立,通过牺牲和违背人们身体当中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和偏好,提倡追求道德目标和遵守社会义务。《白雪公主》似乎就借此表达了一种“模糊情感”,强调如果允许乱伦,那么“家庭就不再是家庭,婚姻也就不再是婚姻了。”[13]61
为此,围绕“谁是最美丽的人”叙述的童话语篇在内容上或可被划入道德寓言,在传统叙事主题和情节上,它属于普洛普的无辜被放逐者的故事。而在当代视觉的空间里,它却超越鞭挞王后的邪恶欲望,以及揭示缺失生母的社会现实和控诉与贬低继母的传统叙事空间,成为凌越女性,讽喻由男性占据支配与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的工具。认识上升到这一层面之后,当我们再次思索为什么国王凝视的对象偏偏是公主,而不是其他女性的时候,也许才会发现,王后与国王通过镜像的隐晦对话打破了正常夫妻关系的语义所指。身份特殊的公主成为“美丽”镜像的主体,不是对以往人们认定的继母虐待行为的谴责,而是反指了王后与国王之间不稳定的夫妻关系,以及后者与公主之间超越社会与家庭伦理常规的父女关系。
福柯在评论爱德华·马奈创作于1863年的《奥林匹亚》时,曾在说明不同的光源、光照/光线、目光与油画里裸体人物的相关性中指出,审美的转变能够在一定情况下引发道德丑闻。[14]35这也可以帮助人们在从童话的叙事空间转向视觉空间,谨慎地聚焦王后的欲望与“美丽”镜像的交互细节时,尤其是深思公主成为王后嫉妒与毁灭的对象这一问题上,发现多次改编后的童话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旨意。它将道德堕落的矛头直指凶残的继母,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道德判断与情感愉悦,但却无疑掩盖了初版中揭示的复杂真相。
这一审美视觉转变似乎使童话里的“谁是最美丽的人”转变为一个述说道德的元语言标记。而王后对它的多次重述则传达出超语言的信息意指。当二者与国王的凝视形成一个符号链,其意指的再功能化则既与国王产生关联,又被赋予指明与延伸的功能,组合出这一标记背后隐蔽关联的人类龌龊欲望内涵。
在《叙述与话语符号学:方法与实践》中,法国学者尤瑟夫·库尔泰曾对格林兄弟的另一则与继母相关的童话《灰姑娘》进行了符号学释读。他指出,服饰与“漂亮的马车”等交通工具是上等社会层次的符号,因为它们含有“豪华”和“阔气”之意,属于“教养”和“富有”之列。原本不起眼的灰姑娘只有在剥离了贫困、屈辱和肮脏,即否定了其低下的个人条件和可悲的仪表以后,才可能与王子有空间的合取,即结婚成为她社会地位升迁的手段。[15]141162
库尔泰的这一阐释使通过婚姻而获得契约保障的灰姑娘与《白雪公主》里的王后拥有了一个重要共同点,这就是女性自身的诱惑力。因此,这两个童话在表现女性以“美丽”吸引王室男性的叙述程式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是,灰姑娘通过不同版本里的仙女/教母/母亲的好朋友等变体的帮助,实现了一个遭受继母摧残的贫贱女孩心中最大的梦想——嫁给王子。而王后的故事则似乎是灰姑娘的续集。她在实现这一梦想之后,又惨遭个人梦想的无情破碎,应验了奠定在容貌基石上的爱情与婚姻必将在前者逐渐丧失之后快速消失与解体的社会生活常规。
这两个童话的另一个相同点则在于它们都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其中的继母对继女虐待甚至杀戮的行为,仿佛不仅是为了强调继母丑陋的社会身份,影射她是“磨难与迫害的制造者”,还象征了继母对“生命之源”[12]12这一女性本原的颠覆,蕴含着对生母身份的回归与期盼。但流行版中不幸失去生母的白雪公主在历经磨难之后,却似乎还将重复演绎王后的故事,因为她让王子无法割舍的依然是容貌之美。
四、结 语
《白雪公主》以童话方式再现了古代已婚上层女性遭受镜像困扰的普遍心理现象。它对“美丽”镜像与女性内心幻象对应的描写与叙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实真相。多个改写版对国王的恋童癖、公主的恋父情节、父女乱伦及王子的恋尸癖等可怕人性缺陷的抹煞,以及将王后的生母身份篡改为继母等,均是为了以人心向善的意旨向读者,尤其是天真无邪的儿童展现一个充满善良、博爱和希望的理想世界。
但正如福柯所说,虚构不在于“让人看到不可见物”,而是要“让人看到可见物的不可见性是多么不可见,”[14]8《白雪公主》的当代流行版似乎完美地实现与阐释了这一虚构。它不仅以人类“既是天使,又是野兽”的帕斯卡程式[16]235,隐蔽地揭示了“继母”的身體和灵魂在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且通过语言的巧妙谋篇布局,使其中的深层镜像信息及其演化倾向得到历史性还原。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William Golding.Moving Target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4.
[3] 格林兄弟.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M].霍涛,等译.北京:友谊出版公司,2010.
[4] 撕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雅克·拉康,等.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M].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7] 维雷娜·卡斯特.童话的心理分析[M].林敏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推荐阅读:论童话带给我们的寓意学术文学论文发表
童话故事是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本文运用文体学的相关理论,从词汇,语法,修辞等几个方面对拇指姑娘进行文体分析,从而可以窥见童话故事的一般性文体特征,拓展文体学研究的空间,也便于创造更多优秀的童话故事。
澹版槑:鈶犳枃鐚潵鑷煡缃戙€佺淮鏅€佷竾鏂圭瓑妫€绱㈡暟鎹簱锛岃鏄庢湰鏂囩尞宸茬粡鍙戣〃瑙佸垔锛屾伃鍠滀綔鑰�.鈶″鏋滄偍鏄綔鑰呬笖涓嶆兂鏈钩鍙板睍绀烘枃鐚俊鎭�,鍙仈绯�瀛︽湳椤鹃棶浜堜互鍒犻櫎.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