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发布时间:2020-12-05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159次
摘 要: 作者:王冰冰 公元1994年12月14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启动,此后,三峡工程成为当惊世界殊的现代科技奇观,是可以从外太空俯瞰到的屈指可数的地球景观之一。 从三峡工程被提上日程始,出于用影像记录、保存完整的三峡之美的迫切目的,大量的自然风光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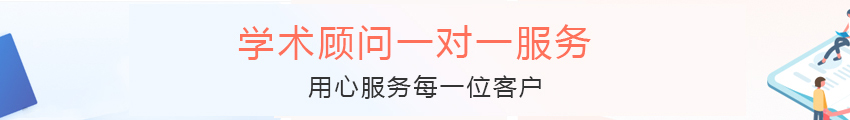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作者:王冰冰
公元1994年12月14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启动,此后,三峡工程成为“当惊世界殊”的现代科技奇观,是可以从外太空俯瞰到的屈指可数的地球景观之一。 从三峡工程被提上日程始,出于用影像记录、保存完整的三峡之美的迫切目的,大量的自然风光纪录片开始涌现,如长达80集的《永远的三峡》(2003),立意便是为三峡山水尤其是那些即将消失的风景“存档”。 同时期的故事片也表达了对于“逝去”的惋惜与焦虑,如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与贾樟柯的《三峡好人》(2006),其间因长江水位升高而注定“消失”的城市“巫山”与“奉节”成为影片的主角,借此传达出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忧虑及一种沉痛迷惘的“乡愁”。 随着三峡工程的竣工,一批聚焦三峡工程的纪录片纷纷出台,如《大三峡》(2009)、《中国三峡》(2012)等。 这些体现国家话语的官方纪录片,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等宏大叙事及现代性的总体性视野中定位三峡工程,将其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政治象征与历史地标。

我们把聚焦于三峡工程的视野向更广阔的时空放大,会看到,作为长江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三峡从屈原的《楚辞》、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开始,就成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情之所钟。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的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风光秀美瑰丽,渗透着巴蜀文化狂放艳异的神秘气息。 迁客骚人往来于此,留下的诗文不计其数。 屈原的山鬼、宋玉的神女、李白的白帝城、杜甫的夔州,可以说三峡的美景与传说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传统,而这些传之久远的诗词曲赋又赋予三峡愈加深厚迷人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以诗词为心”的三峡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美学原乡。 但不同于长城,三峡大坝是现代科技造就的“文明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标”。 至此,三峡的景观融自然、人文、现代科技等因素于一体,成为备受关注的地域文化符号。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影坛涌现出了一批以三峡为背景的优秀故事片,其中三峡景观承担着故事讲述、欲望投射、文化/政治象征等更为复杂的功能。 从“新时期”至今,关于“三峡”这一空间层出不穷的影像生产,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及文化—情感结构,同时记录了民族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问题,丰富了中国及华语电影界关于区域空间美学的生产与表达。 在形形色色的关于三峡的影像生产中,“三峡”这一文化地理空间的意义是丰富且多元的,在自然、人文、历史的价值之外,兼具现代、科技、发展的丰富意涵,“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代中国”[1]三者均在三峡的影像中交融互渗,使其成为巨大的象征性空间及内蕴丰富的隐喻,成为不同“中国叙事”的扭结点。
一、从“神女”到“瑶姬”:“巫山云雨”的现代变奏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影坛涌现出一批以长江三峡为背景的故事片,如《等到满山红叶时》(1980)、《三峡情思》(1983)、《漩涡里的歌》(1981)、《巴山夜雨》(1980)、《神女峰迷雾》(1980)、《飘逝的花头巾》(1985)等。 这些影片有着鲜明的“新启蒙”色彩,批判刚刚逝去的“文革”,赞美年轻人纯洁的爱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歌颂正在展开的“四个现代化”进程。 在爱情故事中,三峡地区的迷人风光成为“浪漫爱”极为适宜的背景,尤其是巫山神女峰,可以说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景点。
在这些以三峡美景映衬青春爱情的影片中,经常会出现船过“神女峰”时的场景,而男女主人公们则往往在此相识(《三峡情思》),或者相恋(《飘逝的花头巾》)。 “巫山云雨”的传说似乎暗合着浪漫与爱欲的主题,但这些充满“新时期”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情”表述却明显偏离了神女与楚襄王间“自荐枕席”“云雨之欢”式的情欲想象。 关于巫山神女的传说,诞生于1980年的《等到满山红叶时》(下文称《满山红叶》)提供了另一则广为流传的版本: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瑶姬私自下凡,流连于巫山的醉人风光,当她看见大禹王挥舞神斧劈开三峡疏导川江,感动于此,便化身巫山十二峰,为往来行船饮水导航,千百年来在此地迎朝晖、送晚霞。 《高唐赋》中巫山神女与楚襄王梦中神交、一夕欢情,因女神与王者的尊贵身份,平添了普罗大众难以企及的绮丽、香艳与神秘,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文人想象。 此后无论是曹植的《洛神赋》还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一脉相承的千古文人/男人的风流梦,传达着他们隐晦的“美政理想”或是纯粹的自恋狂想。 相比之下,《满山红叶》中这个明显经过民间文化改造的传说则颇有几分清新刚健、质朴爽朗的气息,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想象。 瑶池七仙女下凡会爱上普通劳动者而非养尊处优的王公大人,出身高贵的美丽瑶姬却被实干家大禹王所吸引,为他的治水事业助一臂之力。 《满山红叶》通过这个被民间改良后的神话传说暗示着女主人公杨英,美丽果敢的游轮“三副”是现代的瑶姬,而她所倾心爱恋的杨刚正是为了航运事业献出生命的“大禹王”。 对于神女传说的想象在这些“新时期”初期的作品中出现的“变异”,是一处颇具意味的文化症候,体现出多重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化遗产/资源的交织与缝合。 这既是民间文化对文人传统的对抗与对话,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争夺话语空间与阐释权,也是社会主义“十七年”时期政治/文化遗产的显影:即对于劳动与劳动者尊严与价值的强调,爱情需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伦理准则,最美丽的女人与最美好的爱情只属于最“革命”的劳动者/英雄这一美学/政治定律等,均体现出明显的“革命中国”的伦理要求与价值取向。 作为诞生于“新时期”的作品,《满山红叶》显然传达出变革的时代气息,即对于科学、理性精神的推崇,对于“现代化”事业的热切期盼。 影片前半部分通过对杨英高校生活的表现,极力渲染“80年代的新一代”对于航运事业与现代科技的追求与热爱,透露出变化的时代对于知识、文化、现代高等教育与精英文化的信赖与推崇。 相应地,现代“大禹王”的身份也发生了明显转变,从普通劳动者逐渐演变为各种“专家”,如摄影家欧阳明光(《三峡情思》),诗人秋实(《巴山夜雨》),歌唱家江歌(《漩涡里的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秦江(《飘逝的花头巾》)……其实这转变的迹象在《满山红叶》中已经出现,男主人公杨刚虽然是普通信号员,但其“准”大学生的身份和他一直从事的自动化航标系统的开发研制,无疑暗示着这是一个未来的“专家”。
作为有着鲜明过渡色彩的文本,《满山红叶》是社会主义“十七年”电影美学与“新启蒙”文化精神的一次融合与对接,而上映于1985年的《飘逝的花头巾》同样延续了多重话语空间交织与颉颃的特点,且内部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对话结构。 《飘逝的花头巾》根据陈建功同名小说改编,描述了当代青年对事业、爱情、人生的殊异理解与追求。 这部以三峡—北京作为叙事空间的影片,对于瑶姬、大禹王的神话改写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双向逆转:高干子弟秦江与平民女孩沈萍在穿行三峡的游轮上相遇,船过神女峰时他们热情交谈,逐渐萌生好感。 彼时刚考上大学的沈萍意气风发、光彩照人,不经意间竟成了处于人生低谷期的秦江崇拜与爱慕的“女神”。 她犹如瑶姬一般用神力点化了陷入困境的秦江,而后秦江发奋读书,考上了名牌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 在关于“三峡”的段落里,巫山雄奇秀美的风光、奔腾不息的江水、神女峰的迷人传说,与青年人纯洁的情感、欲望及渴望改变现状、追求进步的热情交织在一处,构成一幅水乳交融、互为指涉的“风景”。 可以说这些被瑶姬与大禹王的传说催生出的爱情故事,背后彰显的是对于现代化、科学、进步、个性解放等“新时期”话语的高度信赖与推崇。
可以说这些影片以现代性话语、社会主义伦理重新阐释了“高唐神女”“巫山云雨”这原本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恋想象,对其进行了去情欲化的改写,表达出对于劳动及劳动者的礼赞,对于科学、启蒙、现代化的推崇,同时用唯美抒情的镜头语言传达出“新时期”理想的爱情及女性观。 但与《满山红叶》不同,《飘逝的花头巾》与《三峡情思》中,爱情故事出现了某种变奏,掺入了不和谐的杂音,在叙镜中这来自于“瑶姬”的动摇甚至幻灭。 大学生沈萍与画家黎青都陷入了“个人主义”小圈子,染上了功利主义及贪图享乐的毛病,从大禹王的“帮手”、精神伴侣逐渐转化成了“被拯救者”。 沈萍与黎青的蜕变甚或堕落与空间的转换息息相关:萌生于神女峰下的纯洁且热烈的爱情,一旦脱离了这一区域进入城市空间,就会发生萎缩甚至变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或曰警示。 对于黎青来说,上海意味着安逸舒适的“小日子”,而对于欧阳明光,三峡则代表着理想、激情、灵感与充满创造力的生活,是“大理想”。 二人的分歧或者说上海与三峡的空间对立,正是物质与精神、理想主义与日常生活间的尖锐对立,而在《飘逝的花头巾》中,北京与三峡间的空间差异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在影片的开头部分,镜头在三峡与北京之间来回切换,入画的分别是三峡的风光、江边的纤夫与高等学府图书馆、机房中的莘莘学子,交叉蒙太奇指涉着两处不同的地域空间: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 北京代表着现代、知识、科学与进步,三峡则似乎指称着前现代、东方亚细亚式的生产—生活方式。 秦江与沈萍先后在北京陷入人生危机,而在三峡时的他们则是意气风发、纯洁快乐,三峡对于秦江而言始终是一种拯救的力量。 当他返回北京后,每当陷入精神困境时都会凝视书桌旁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无疑在以这种方式警醒自己。 在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高歌猛进的时代,为何现代性的北京却需要前现代的三峡的拯救? 如前所述,正因为“三峡”作为多重文化符码交织的空间,在影片的叙镜中不仅象征着前现代/传统中国,同时还是“革命中国”的表征。
二、从“人民”到“底层”:“纤夫”群像的变迁
“纤夫”的群像,在“新时期”以来关于三峡的电影及纪录片中,往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符码,与“巫山神女”的传说一起结构着人们对于三峡及长江的想象。 在《飘逝的花头巾》中,三峡作为重要的叙事空间,始终与“纤夫”的群体形象互为指涉,不仅在开头与结尾前后呼应地出现纤夫在烈日下拉纤的场景,且每当秦江在北京回忆起三峡时,画面上总会出现衣衫破旧、皮肤黝黑、骨节变形的纤夫——他们在江边的沙地或岸边的峭壁间艰难行进,似乎每一步都负载着人生的苦难与历史的重负。 电影镜头暗示着纤夫的形象已经内化于秦江对于长江/三峡的认知与感受,而被他一直贴在案头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油画,俄罗斯画家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73年所作)则指涉着他的知识谱系与想象来源——那是作为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重要外来文化资源的俄罗斯及前苏联文学艺术。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秦江在记忆与想象中将三峡的纤夫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形象叠加一处,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的叠加与置换中,他完成的是一次对于自我的想象与重塑,也就是将自己与俄罗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并置。
“纤夫”作为长江景观的象征,既指“民生疾苦”,又是“人定胜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支撑的对于底层劳动者及民间的想象,其间交织着“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及“革命中国”的繁复因素。 这也是《飘逝的花头巾》中,秦江对于“纤夫”及“三峡”的复杂情感之来源。 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宾作为自己的理想镜像,无疑是彼时高蹈的启蒙思想赋予其“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反抗强权的艺术家的自恋想象,但与其说他是在高高在上地怜悯与批判,不如说他是一个时刻需要回归大地以汲取力量的大神安泰——“三峡”于他而言,不是北京之外的生活调剂,而是地母盖娅博大温暖的怀抱。 “纤夫”是底层苦难的象征,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同情内在于“新时期”人道主义的话语系统与文化逻辑,但文本中传达出的对于纤夫群体中蕴藏的潜力与伟力的崇拜,亦在借重“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工农兵文艺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的经典表述。 同样,在批判“文革”的经典之作《漩涡里的歌》、《巴山夜雨》中,“三峡”中的急流漩涡象征着凶险的政治风波,而逆流而上的纤夫、穿行江中的“水猫子”、游轮中的普通乘客则象征着群众、人民的力量,而来自他们的支持与庇护,是歌唱家江歌、诗人秋实最终获救的关键。 用学者戴锦华的话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仍然以某种方式延续在80年代的文化脉络中”,“七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话语,始终借重并重叠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遗产”。 [2]
作为内蕴复杂的时代文本,借助民间道德伦理与“革命中国”的文化遗产,《飘逝的花头巾》以“三峡—北京”的空间对立模式,在一个将启蒙主义现代性作为神话的时代,却有能力批判现代性中的负面因素,或者说将现代性内在的矛盾性初步展露出来:“它既是人的意识或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一刻,又是人类工具化、客体化过程的开始”[3],或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用诗意的语言表述的现代性之二重性: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既经历着不断被客体化、物体化异化——一个主体性不断分化丧失的过程,同时又经历着主体世界的开拓、觉醒和自觉,以及历史的自我意识生成的过程”[4]。 如果说在“新时期”初期,现代性中为主体提供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尚且大过其负面效应——异化、物化的威胁,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失望地发现,现代性关于美好未来的承诺却并未如期兑现。
新世纪之后,贾樟柯用准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了《三峡好人》(2006),彼时“纤夫”的群像已经被更为庞大的“打工者”群体取代,他们的身上不再交织着繁复的隐喻,不再是多重意识形态话语借重甚或争夺的空间,而仅仅是“底层”的代名词而已。 《三峡好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英文名字Still Life,意即“静物”,借此指涉以韩三明为代表的广大底层。 在叙镜中他们始终眼神迷离空洞,举止呆滞迟缓,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方能表明尚是“活物”。 他们就是遽变时代中的一群“静物”,虽然在他们的手下,一个又一个的“奉节”或“巫山”在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急速推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社会资源的重组,在影片的叙镜中那是在黑白两道游走的“大哥”郭斌,始终未曾露面却仿佛主宰一切的厦门女富商丁亚玲,以及云集在俱乐部里歌舞升平的社会精英[5]。 虽然贾樟柯将影片的背景放置于因三峡工程而即将消失的城市“奉节”,但一如既往地,他关注的时代事件却不仅仅是“移民”,而是“下岗”:三峡库区的企业在破产、兼并、改制与重组的过程中发生的劳资关系危机,由此导致社会分化的加剧。 影片中断臂人和他沦为暗娼的妻子的悲剧,其背景正是整个“90年代”的历史缩影。 这些曾经的“工人阶级”,即使没有移民事件,他们也注定要离乡背井,沦为和韩三明一样的打工者。 作为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代价”,韩三明与断臂人们在一夕之间沦为底层,成为弱势群体,除了沉默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作为GDP高速增长时代不合时宜的“静物”,他们疲惫、麻木与冷漠的背后,是否也曾有过不甘与愤懑? 人们无从知晓,作为当下中国底层“代言者”的贾樟柯,他选择了“准纪录片”的方式,只是忠实或被动地记录下这一切,让观影者/读者们“自己去看”、去判断。
从“纤夫”到“打工者”及“底层”,命名的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是政治理念,涉及“劳动”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根本性命题。 在“新时期”的“三峡”影像中,“纤夫”却是“人民”与“劳动者”的代名词,而在社会主义伦理体系内部,对于“劳动”的高度肯定,联系着中国下层社会主体性建构这一时代命题:“在20世纪的左翼思想中,‘劳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也是伦理与情感的”[6]。 在“革命中国”的语境中,“劳动(主要是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曾经使中国下层社会获得一种主体性以及相应的阶级尊严”[7]。 由此可见,正是这样的政治理念与社会伦理在“新时期”的延续,使得一系列关于“三峡”的影片保持了对于“劳动”与“劳动者”的高度尊重,从对于“巫山神女”传说的改写,现代“大禹王”形象的重塑,到用饱含崇高美学的诗意镜头呈现“纤夫”群体。 由此可见,“革命中国”的文化遗产仍然是“新时期”精英知识分子重建主体性的重要文化资源。 而对于秦江、欧阳明光、秋实、江歌而言,与其说他们表现出的强大的主体性是依靠从人民/民间汲取力量,不如说是彼时多重话语空间及多样文化资源赋予他们言说/批判的自由与力度。 在一个被变革的激情充溢、因未来的视域被充分打开的大时代,过去、现在也显现出了别样的维度与价值,使人们暂时超越他们所属的历史瞬间,而具备了可贵的反省批判与自我否定的精神。 到了贾樟柯《三峡好人》的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巫山神女》(1996)、《她们的名字叫红》(2012)、《长江图》(2016)等关于三峡及长江的文艺电影中,不难发现伴随着“历史的终结”、未来视域的封闭,人们的“当下”或曰现实感逐渐消失。
三、“神女”的复魅:现代性的“终结”
随着“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完满竣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体现国家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纪录片,如《大三峡》(2009)、《中国三峡》(2012)等。 在这些颇具史诗风格的纪录片中,三峡工程往往被表述为一个“奇迹”,是发达的科技与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共同造就的奇观,其背后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20多年GDP高速增长的奇迹。 有了三峡工程,“三峡”便不仅仅是长江文化的象征,关于三峡的梦境也不再局限于“高唐云雨”,而是持续了百年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梦”“强国梦”,可以说“三峡大坝”就是中国现代性登峰造极的仪式性表达,是一座现代科技文明的丰碑。 按照马歇尔·伯曼的现代性想象,三峡大坝就是典型的“浮士德式的发展模型”,即大规模的长期发展的工程,“注重的是巨大的能源和一种国际规模的交通工程”; “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润”(即“利在千秋”),而“浮士德式的发展模型”所要满足的,正是“现代人对历险性的、无止境的和永远更新的发展的持续需要的能力”[8]。 从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三峡工程的雏形构想始,可以说这无止境的现代性渴望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而当现代性的辉煌梦境终于迈入巅峰时刻、当下的中国成为新兴的现代化经济实体时,人们却开始将愈发疲惫困惑的目光转向“怀旧的乌托邦”,“怀旧病者”逐渐取代过往那种浮士德式生机勃勃的“发展者”与“规划者”。
综观同时期的关于三峡及三峡工程的文艺电影,无论是章明的“巫山三部曲”(《巫山云雨》《秘语十七小时》《巫山之春》)及《她们的名字叫红》,还有杨超的《长江图》,都被一种“想象的乡愁”笼罩着,它“颠倒了幻想的时间性逻辑,创造出比单纯的羡慕和模仿、欲望还要更深层次的愿望”[9]。 这愿望是对于传统中国或曰古典中国深刻却不明所以的向往,首先体现于对“巫山神女”形象的再度改写。 在《巫山云雨》中,“巫山云雨”再次成为人神交媾的情色隐喻,相应地,“巫山神女”的形象也被再度情欲化,直到化身为真正意义上的“神女”/妓女——《长江图》与《她们的名字叫红》中女主人公的身份直接就是性工作者。 “新时期”辅助大禹王的“瑶姬”们那健康爽朗、朴素清新的形象一去不返,无论是杨青(《巫山云雨》),还是安陆(《长江图》),都是眼神迷离、唇褶婉转的性感美人,她们是从《高唐赋》《神女赋》或《楚辞·山鬼》中直接走出的“尤物”,充满前现代的原始与神秘,携带着难以言传的性魅惑。 神女形象的“复魅”,完成的是一次想象中的文化对接,编导者试图回归以屈骚为代表的中国雅文化源头,回到屈子贾谊、唐诗宋词,回到《牡丹亭》《桃花扇》及纳兰词的浪漫主义古典世界。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畅游长江时,想象将来三峡大坝建成后的壮观景象:“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曾经被“革命中国”强烈的现代性追求所截断的“巫山云雨”——古典中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在“世纪工程”开始施工及最终落成的时代,却在关于“三峡”的文化文本中全面回归,这不能不说是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症候。
实际上,渗透在《巫山云雨》《长江图》中的“想象的乡愁”,与其说是指向三坟五典、百宋千元的古典中国,不如说是传达出一种当下正在全球蔓延的“回到子宫”的“逆托邦”(retrotopia,又译为“怀旧的乌托邦”)冲动,如《长江图》在宣传海报中所泄露的企图与欲望:“蜿蜒的长江像一具横陈的女性的身体,而一艘船正在逆流而上。 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既是征服,也是回到母体的子宫”[10]。 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解释,当所有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都不再具有可信度与吸引力时,“过去”则成为值得信任的对象,人们遂通过虚构出的美好“过去”抵御“现在”与“未来”。 “逆托邦”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于缺乏魅力的当下及不确定未来的焦灼与恐惧,是现代初期积极的、坚定的和自信的乌托邦受挫之后,人们逐渐产生退出外部世界的危险欲望。 [11]《长江图》用缓慢的运动长镜头营造出水墨长卷般的“长江图”,那阴郁清冷、萧瑟空灵的氛围无疑在致敬中国古老的绘画艺术,但影片中作为灵魂存在的“诗集”,却无疑指涉着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诗人自戕、理想放逐的时刻,对于时代的疏离与弃绝才是男主人公高淳选择逆江而上、回归母体/子宫的缘由。
《长江图》犹如一个超载的寓言,用文化、宗教、民俗的糖纸包裹着政治的果核,而高淳逆江而上的行程,是回避世界与他人的精神“逆旅”,抚慰他的只有诗歌和被诗歌唤生出的“神女”。 当年的《满山红叶》《三峡情思》《飘逝的花头巾》与《漩涡里的歌》,都试图大声地告诫年轻人,不要陷入个人主义的小圈子与利己主义的小宇宙,那会窒息了才华、毅力与思想,要到广大的天地中去,到人民中去,到纤夫中去,融入生活就像融入三峡的山水。 其自信、理性与激情,源自于对一个更美好、更合理未来的信念与信心,也是源自于对“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内部丰富遗产的自觉继承与合理调用。 而《巫山云雨》《长江图》则陷入主体性的精神危机,在自恋的“怀旧病”中难以自拔。 面对发展时期的巨大命题,如何恢复历史的纵深与未来的“光晕”,创造出符合大多数人需要、愿望与梦想的世界,如何让高淳重新变回秦江、欧阳明光,从自恋的那喀索斯回到极富创造力、行动力与想象力的皮革马利翁或浮士德? 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必须被尽快纳入到关于未来的议题之中,因为一如齐格蒙特·鲍曼并不乐观的预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共居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生死抉择的关头:我们应相向而行,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前进……”[12]
【作者简介】王冰冰:文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注释:
[1]“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参见蔡翔在《革命/叙述》中提出的一组颇具启发性的概念,“革命中国”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 “现代中国”是与“革命中国”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亦即“资产阶级现代性”。 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某种公开或隐秘的历史关联”。 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7页。
[3]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4]〔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5页。
[5]张伟兵:《变迁时代的命运轨迹与社会公正的表达——评电影〈三峡好人〉的本质与价值诉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7]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第274页。
[8]〔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放松缰绳的现代性》,转引自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9][10]王颖:《〈长江图〉:芜杂的叙事和弥漫的欲望》,《艺术广角》2018年第2期。
[11][12]〔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179页,第230页。
相关期刊推荐:《书画艺术》是具有学术性与普及性廉融的中国书画篆刻专业刊物,为适应新形势,充分调动社会办刊力量。《书画艺术》有以下几大看点:封面设计新颖独特、《画坛名家》一栏推出二人、《书坛名家》一栏推出二人、《印坛名家》一栏推出一人、《经典重读》一栏推出一篇大文章、《大师回顾》一栏推出新人力作、《艺林漫步》一栏推出别具一格的瓷俱作品:。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