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发布时间:2021-05-10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167次
摘 要: 摘要:对于人文纪录片与人类学影像这两种似乎判然有别而又彼此关联的话语类型,做太明确的区分有没有必要?从学科属性上看,人文是个太宽泛的词,人类学也不一定只是科学。从叙事方式看,梅索斯墙壁上苍蝇式的拍摄未必客观,把镜头转向自我未必主观。从作者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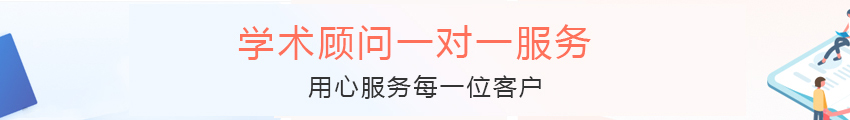
摘要:对于人文纪录片与人类学影像这两种似乎判然有别而又彼此关联的话语类型,做太明确的区分有没有必要?从学科属性上看,“人文”是个太宽泛的词,“人类学”也不一定只是“科学”。从叙事方式看,梅索斯“墙壁上苍蝇”式的拍摄未必“客观”,把镜头转向自我未必“主观”。从作者及作品看,人文纪录片未必不涉科学,民族志影像也有多种面孔:有的强调科学性,有的强调人文性;有的是局外人角度的“客观”记录,有的是局内人主体性的描述;有的拍成论文,有的犹如故事片;有的第三人称冷冰冰一本正经,有的第一人称带着体温和感情……所以,以人和问题为出发点,法无定法的影像叙事,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关键词:人文纪录片;视觉人类学;科学与人文;问题意识;影像叙事
人文纪录片与人类学影像共有的关键词,就是“人”。但为什么“对视”起来了呢?本次会议①的学术旨趣,是基于“在科学与人文的交叉点上,人类学影像与人文纪录片属于两种判然有别而又彼此关联的话语类型”的判断,从而提出了“人文纪录片与人类学影像的对视与交融”这个主题。笔者推测其潜台词大概是:人文纪录片偏于“人文”,而人类学影像偏于“科学”,判然有别,所以“对视”;而两者的对象又都与“人”有关,彼此关联,所以也会产生“交融”。
问题是,这样的区分有必要且可能吗?
一、学科属性
从学科属性上看,“人文”是个很宽泛的词,“人类学”也不一定只是“科学”。它们的差异,似乎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但一面对实例,却发现它们之间的“交融”,可能大于“对视”。
“人文纪录片”,学科属性比较模糊;“人文”一词,容量太大。按现行学科分类,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学等都属于人文学科,且有不同的认知取向和方法论。如果“人文”加上“纪录片”,或可理解为以某种人文角度拍摄的纪录片。印象中的人文纪录片,一类比较“主流”和大众化,比如哲理片、历史纪念或历史掌故片、文化专题片、旅游片等,大致可以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中偏于人与文化“纪录”类的电影电视类型;另外一类比较“边缘”和小众化,大多以独立纪录片的身份出现,制作者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对底层人群的关注、对人性的直面和对历史的反思,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
人类学影像似有相对明确的学科属性,这就是用影像记述的民族志或用人类学方法拍摄的纪录片。但人类学又是一个兼涉多个学科领域的整合性学科。它有时被归入法学或社会学,有时统辖考古学或民族学,有时挂靠在人文学院,和哲学(哲学人类学或认知人类学)、历史学(历史人类学)、语言文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以及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视觉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绘画人类学等)打得火热,有时又到生科院、医学院、地理学院,甚至工科的建筑学院串门,把生态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建筑人类学等弄得科学份儿十足。要不就直接针对焦点问题,像记者般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的灾难人类学家,像间谍般研究敌国文化模式和社会心理的跨文化人类学家,像在艾滋病、新冠病毒防控现场的医学人类学家。
人类学和社会学貌似相近,常常被合并在一个学院。但社会学家出门,不是召集会议,就是分发问卷,研究报告里充满数据和公式,一身“科学”行头;人类学家出门,背包里藏个相机,手揣裤兜里,东游西荡,混吃混喝(我们带学生做田野考察实习,进村后,谁能最先蹭到老乡的饭,就知道他有戏了),喜欢听八卦、包打听,常常被误认为是记者或是“上面”派来的调查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要有故事”“写有温度的文字”,成为一些老师教育学生怎样写好学位论文的口头禅。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昆明参加一次人类学国际会议,有国外学者提出了人类学不是科学陈述而是一种人文表达的说法,很得人心;学界有人甚至认为,民族志写作要表达诗意和叙述性的事实而不是科学事实。①著名学者林耀华将其人类学代表作《金翼》写成了小说,他的弟子庄孔韶以诗入学,近年来又在折腾表演化的人类学影视,和画家合作搞绘画人类学。
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对象,主要相对聚焦于人的文化,特别是乡俗的、底层的、少数族群或简单社会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纪录片中的独立纪录片精神有所相通。近年也有研究白领阶层、高能物理社区、海外民族志、流行文化和网络社会的佳作,反映了人类学与时俱进对复杂社会进行研究的学术拓展。
而说到人类学影像,在学科的不同语境中,它们会被不同地表述:民族学电影、民族志影像、影像文化志、影视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电影社会学,等等。很多情况下,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还有很多非人类学部门设立的人类学影像项目,比如文化和旅游部的“节日影像志”、国家图书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和“史诗工程”等,其理论指导和田野工作方法是人类学的,在实践上也是把不同学科通过影像,“对视与交融”起来了。
人类学因和影像结缘,从理论、实践、技术、工具到传播方式,与传播学靠得很近。传播学是麦克卢汉无中生有创立的学科,但关于影视的拍摄实践和理论探讨,却在照相机电影机发明之后就开始了。影视手段,最初是作为一种工具,被探险家、旅行家、艺术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广泛使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像不过是作为游记、考察报告的附图或艺术家参考的素材,后来被折腾成具有展览和票房价值的作品、流行文化的广告,升华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宣传工具,占据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像的力量,被金钱和权力控制之后,在全球化时代尤为凸显。“眼球经济”“视觉政治”无孔不入。还在坚守一点“文化”的,比如纪录片,变得珍稀起来。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文纪录片和人类学影像,都是碎片化“读图时代”处境微妙的幸存者。
现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影像在人们生活中无所不在。图像大量生产,不断覆盖,海量影像信息,形成碎片化瞬间化的奇观世界,也促进了影像平民化的进程,引发了媒介人类学的崛起。虚拟社区、赛博空间、人机交互……让人眼花缭乱的人文、社会、科技大混杂,更是界限难分、虚实互融、时空穿越。比如最近热度很高的美国大选,无论线上线下发生什么事,立刻传遍全世界。据微信群里传出的一则消息(据说来自《纽约太阳报》):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女巫正在网络上集结,计划在2020年10月31日万圣节和11月2日集体作法念咒,要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败选。这些女巫用#BindTrump和#MagicResistance主题标签串连起来,发动名为“蓝色浪潮”(BlueWave)的咒语攻势。①这个消息是否可靠不重要,女巫+网络+特朗普(可能还要加上特朗普的“护法”福音派),越来越多的类似信息,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魔幻了。
二、叙事方式
按刻板印象,人文纪录片与人类学影像既然有人文与科学的差异,其叙事方式,好像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差异。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觉。
为了追求“客观”,梅索斯兄弟曾把自己的拍摄方式比喻为“墙壁上的苍蝇”,也就是对拍摄对象不做任何干扰,不带主观意图。但我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做到。特别在《灰色花园》中,两个大男人扛着电影机进入独居已久的两个女人家里,不可能成为“墙壁上的苍蝇”。还在拍摄中,被拍摄对象就已经在镜头前表示爱上了持机的大卫·梅索斯,拍摄者也打破自己的规则,进入了镜头。有人曾向笔者吹嘘,他的镜头是百分百客观的。笔者就问他片比。他答50∶1,笔者问,那剪掉的49呢?谁剪的?为什么剪?
相关期刊推荐:《民族艺术》于1985年创办,全刊信息多却有条有理,坚持打造交流思想和经验共享的主流平台,重点刊发各类关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
笔者比较反感那种自以为“客观”的书写方式。进入他者的世界,哪怕同吃同住一年半载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所受教育,都不可能使你变成他。即使我们提倡努力站在“文化持有者”的立场,也多半是一厢情愿的良好“努力”而已。为了显示“客观”,不少人类学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常常连“我”字都不敢出现,刻意回避“我”的存在。明明你在现场,却要做出不在现场,以上帝式的眼光俯视或旁视对象的姿态。这不很虚伪吗?至少也是一种虚假,与“客观”无关。
近三十年来有很多把摄影机交给村民的实验,比如20世纪90年代云南的“农村妇女写真”、21世纪后风起云涌的“乡村之眼”“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农民工自拍”等,呈现了另外一种视角——主位的视角,也产生了不少精彩的作品。但如果用所谓“客观”“主观”来说事,也会陷入和外来拍摄者一样的陷阱。记得2004年“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的村民第一次拿起DV时,“代表10亿农民”的信心爆棚,下意识模仿《焦点访谈》,试图以影像反映现实,并以此改变现状。结果可想而知。
甚至把镜头转向自我,更难用所谓“客观”“主观”来定义。就像照镜子或照相一样,在镜头前,人会下意识地修饰打扮,进入表演状态。是整容伪装,还是一丝不挂,取决于他(她)想扮演什么角色,想呈现哪方面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私影像”进入的内在“现场”及其所反映的真实,又是局外人很难达到的。
人类学影像以人和问题为出发点。这个“人”,包括他和我、外和内、群体和个人;人的“问题”,有生计问题、心理问题、健康问题、族群问题、阶层或阶级问题,等等。面对不同情境中的人及其待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当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处理方式。即使进入他者的世界,反观的,也是自我的镜像。我带着我的问题寻访他人,所谓“问题意识”,其实是与自己习得的有关学术的、文化的或人生的思考。那些“问题”,基本是自拟的,或者自己所学专业教的。这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主观者”。作为人类学经典文本的《忧郁的热带》,不过是一个叫列维-斯特劳斯的家伙,烦了巴黎的现代化,想到地球的对拓面去寻找失落伊甸园的写生记事本;而那位确立了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的马林诺夫斯基同志,他自己关于田野考察的“科学”报告和个人日记所呈现的两种真实,你说得清它们之间何为主观、何为客观吗?
和文字叙事一样,影像叙事也是没有固定方式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纪录片还是人类学影像,都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过不同的风格流派。大家熟知的,有弗拉哈迪式的在一个地方讲一个生活故事(比如《北方的纳努克》《摩阿娜》《亚兰岛人》),有维尔托夫战斗号角式蒙太奇(比如《执摄影机的人》《关于列宁的三首歌》),有格里尔逊画面加解说式的宣传片,有米德和贝特森把影像的运用作为民族志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关于巴厘岛田野考察的系列影片),有让·鲁什式以问题进入访谈(如《夏日纪事》)和共谋式拍摄(从《我是黑人》以来的大量实验),有梅索斯兄弟“墙壁上苍蝇”式的直接电影,有瓦尔达自言自语式的拾零捡碎,不经意间就推动了一波哲理散文电影的新浪潮(比如《拾穗者》)。在国内,短短几十年间,纪录片人也尝试过百年影像史的几乎所有套路。仅以笔者有限的参与拍摄或独立拍摄经历为例,就围观过摆拍(20世纪70年代跟班电影厂,看他们怎么制造伪民俗纪录片),写过画面加解说的脚本(20世纪80年代的《生的狂欢》),记录过一种特殊民俗(20世纪90年代的《普吉和他的情人们》)、一个民族习俗或家庭的影像实录(比如《高原女人》《高原上的民族》系列片),也尝试过在学术记录中讲述人性的故事(2004年的《布依摩公》《没顶的房子》《十二岁当家》),以及长镜头直接跟拍(大量田野考察实录),参与VR全景影像等新媒体尝试,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这就是米德和贝特森提示的,我们的田野叙事和拍摄、编辑,应该详细说明摄影环境,比如被拍摄者在摄影机前的反应,摆拍与花钱请人表演的区别,拍摄和剪辑时的选择,修片问题等。①我们许多拍摄者关心的主要是拍出一个“完美”的作品,至于如何拍摄,如何剪辑,PS了没有,却好像成了商业秘密。而被拍摄者事前和事后的反应,更是很少有人愿谈。事实上,拍摄者参与程度、被拍摄者反应和拍摄环境等说明相当重要。我们永远不要装作自己不在现场,不要以为躲在镜头后面就可以冒充客观。当我们进入现场,我们这些外人以及吓人的机器,就已经侵入和干预了拍摄对象。被拍摄者对我们及其镜头的反应,正好是田野中一个当下的事实。我们的在场影响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我们的镜头对准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已经由拍摄者选择了;到剪辑的时候,留下什么?删去什么?甚至时间顺序调整一下,结果就完全不同。这是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的关键问题,但很少有人记录和公开这些过程。②如果在作品中呈现,则会被视为败笔,要冒很大的伦理风险,遭致多方批评。例如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拍摄佤族民族志纪录片《拉木鼓的故事》。我们的计划,是拍摄一个能够反映佤族文化的典型事项。请教佤族“窝朗”(大头人),他毫不犹豫地说:“木鼓!木鼓是我们阿佤的魂。”但佤族拉木鼓仪式由于伴随猎头活动,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禁止了。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当过县长的老“窝朗”给县人大提交了一份提议,希望恢复佤族的一些传统文化,木鼓自然在列。老县长怀揣县里批复同意的红头文件,正想借此打开局面。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直接到了一个未被媒体骚扰过的佤族村寨,老县长召集村民开会商量拍片的事。村民的问题是:“恢复拉木鼓,砍哪个的头呢?”老县长解释不砍头,只拉木鼓,村民担心:“恢复一样,不恢复一样,怕不好,鬼会怪。”老县长一再强调,这不是真的搞,而是拍电视,人家出钱宣传我们佤族文化。经过反复动员,出于对大窝朗和老县长双重身份的尊重,村民好歹同意了。在拍摄仪式搬演的过程中,我们却拍摄到了很多意外的真实:用传统方式(鸡毛信)和红头文件与村民沟通的老县长,和摄制组讨价还价的被拍摄者,深夜来访欲言又止的村民,在仪式时间、与人和鬼神的沟通方式、祭祀用牺牲(牛)选择及分配上的争论,意外天气变化导致的恐慌等。摄制组及时调整了拍摄方案,不仅记录搬演的仪式过程,同时把在动员、实施、发生问题的过程及村民的反应和指责也记录下来。最终成为一个拍摄搬演仪式,却记录到了隐藏在村民心底的民间信仰现实,成为呈现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互动过程中文化建构复杂性的纪录片。如果从仪式真实的角度看,这次活动是搬演的;但如果从心理真实的角度看,那种一直存在于村民心中,随时可能被唤醒的原始巫性,那种传统和现实错综复杂的关系,被一次拍摄事件引发并显露无遗,作品又是非常纪实的。类似叙事方式,还有刘晓津、郭净大约同时期拍摄的《关索戏》。拍摄者一开始也是以记录一种民俗事项的初衷进入田野,后来发现去的时间不对,人家已经做过仪式。为了拍摄,他们只好出钱请村民重新来一遍。这类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是在村里拍摄,由村民表演,但它没有伪装自己拍到了一次真实的仪式,而是如实记录下搬演的全过程:如何讲价,没拍好的镜头怎样反复补拍,以及无意间发现“给你们拍”的内容和他们自己“用”的有所不同。
这类作品,没有回避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互动的过程,没有掩饰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的反应及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反应及发生的问题不一定愉快的时候,还能如实记录。遗憾的是,这种正视田野现实的勇气、表述方式和内在意义,至今还没有多少人理解。而作品隐含的问题意识,比如被拍摄者对拍摄者及其摄录镜像产生的特殊认知,更需具有对学术问题敏感的发现能力,比如胡台丽通过对民族志纪录片《矮人祭之歌》田野考察经历的回顾,讨论了台湾赛夏人在仪式过程中产生的几重“叠影”现象:死者和生者、我族和外族、人和植物、人和灵、灵和灵、不同时空的祭祀或表演对象等,都在不同的情境中发生“叠影”。特别是当某个人的意外死亡,被归咎到与外族人拍摄了他们的仪式有关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微妙。由于历史原因,与外界恩怨交织的情感,是许多族群的文化主题和认知惯习。亦敌亦友的他我关系,使彼此隔离的族群边界出现了一个模糊地带,从而形成不同形式的“叠影”。这种“叠影”,其实是历史与现实时空中的社会系统、族群关系和文化心理的复杂投影。①它们可能被归咎于任何偶然事件,而外人及其曾被视为能够“摄魂”的摄影机的进入,就是引发这种危机的最大由头。——论文作者:邓启耀
濠㈠湱澧楀Σ锟�:闁冲墎濮甸弸鍐偖椤旇姤闄嶉柤濂変簽閻擄紕绱旈幋娆屽亾娴g儤妯婇柡鍜佸枔閳ь兛妞掔粩楣冨棘閸︻厾鎼兼俊顐熷亾缂佷究鍨洪弳鐔煎箲椤旇偐姘ㄩ柨娑樼焷椤曗晠寮版惔銏℃嫳闁哄倸娲ㄧ亸鐐差啅閼碱剛鐥呴柛娆愬灱閵嗗啰鎲存担绋跨亖闁挎稑鏈导鍐窗濠娾偓缂嶆棃鎳撻敓锟�.闁冲灈鈧剚娲ら柡瀣矋閸嬪秹寮伴娆戠▕闁兼澘鎳嶇粭鏍ㄧ▔瀹ュ棗鍘掗柡鍫墮闁解晠宕i弶璺ㄦ綌缂佲偓閻戞ɑ鐎柣姘煎枙娣囧﹪骞侀敓锟�,闁告瑯鍨垫禒鍫㈠寲閿燂拷閻庢冻闄勫﹢铏亜妤e啯锛�濞存粌鐗呮禍鎺楀礆閻樼粯鐝�.
SCISSCIAHCI